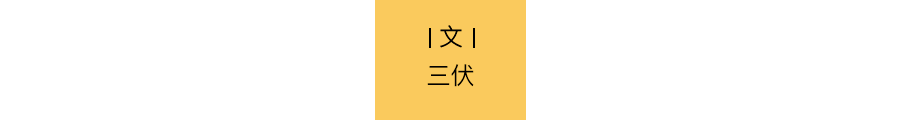毒贩在我身旁,突然拿出了枪


独家抢先看
当地时间2月3日,一列运载有多种有毒化学品的列车在美国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城脱轨并引发大火。
6号,美国环保局宣称,为了防止爆炸,盛有氯乙烯的5节车厢被“故意打破”,其中的氯乙烯被转移到提前挖好的沟渠中焚烧。
黑色烟雾在空气中上升,暗藏的危险早已蓄势待发,当地民众称其为“美国的切尔诺贝利”。
这是目前国际上的一桩重大安全事故,看得见的残骸还停留在事故现场,看不见的恐慌已经蔓延到了大洋彼岸。
俄亥俄州危险材料专家公开表示,此次事故相当于是“用化学物质毁了一个小镇”。
2月15号,毫不意外,央视记者刘骁骞出现在了列车脱轨现场。
他只简单地佩戴了防毒面具,眼睛通红,站在离火车残骸仅几米远的地方,探访了美国官方始终搪塞的最新进展。
这不是刘骁骞第一次身临险境了。
驻外十余年间,他跟随警察拦截过运毒的车辆,暗访过边境的走私枪支黑市,采访了里约热内卢的贩毒集团,还曝光了“银三角”的可卡因制作工序……
在哥伦比亚时,他去反政府武装营地探访,把脑袋别在了裤腰上;驻美国后,他是第一批采访被警察“跪死”的弗洛伊德的家人的记者之一。
他称自己的工作为“长线报道”,有些故事或许并没有最终结果,但血淋淋的过程就足够触目惊心。
当要形容这个漫长的故事,刘骁骞引用了一句歌词:
“我不知道何为终点,我向死而生。”
刘骁骞探访列车脱轨现场
提到刘骁骞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还觉得陌生。
在很多他本人出镜的报道中,下面的评论几乎都在提及一件事——这是那个采访毒贩的“奶音猛男”吗?
那就先从这个,让他“一战成名”的故事说起吧。
刘骁骞采访毒贩
2012年,身处巴西的刘骁骞收到了一封邮件,里面附带了一张彩色照片:
两个深色皮肤的人骑着一辆摩托车,后座的人手里还拿着一把枪,毫无疑问,是毒贩。
发邮件的人写道,自己知道刘骁骞是中国的驻外记者,也知道他对治安题材非常感兴趣,可以提供一些独家照片。
只是,两人素不相识,刘骁骞并不敢完全信任对方。
刘骁骞驻拉美期间(下同)
两人正式产生交集,是在2014年。
世界杯的举办让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事实上,打开真实的里约地图,它更像是一个爬满了虱子的华美长袍。
这里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狂欢节,有美丽的桑巴,动感的音乐和闻名全球的足球文化。同样,这里也存在着736座贫民窟,是贩毒集团的天下。
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在里约,地狱和天堂之间只有十分钟的路程。”
此前,刘骁骞已经做过多期关于毒品枪支问题的专题节目,试图拼凑出完整的贩毒链条,将这个城市被涂抹的一面展示出来。
如此一来,不采访到毒贩本身的话,刘骁骞总觉得有些遗憾。
于是,他联系了给他发邮件的那个人——经过长达一年的接触,他决定要相信这个线人。
采访毒贩,听起来就是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过程却远比想象的还要惊险。
在2002年,巴西环球电视台的一位调查记者就因偷拍了贫民窟的一个露天毒品集市而遭到了毒贩的打击报复。
他收到了民众的举报,去调查一个涉及未成年性交易和毒品交易的舞会,等他再次出现在世人眼前,是几块被烧焦的人体残骸。
据后来被逮捕到的犯罪嫌疑人描述,这位记者在生前,遭到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
该事件的相关报道
也有人问过刘骁骞,知不知道暗中拍摄的后果是什么?
刘骁骞说,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当场被发现,然后被处决,另一种可能是,“素材播出后,毒贩会来找你”。
所以,他必须要得到允许。
线人将刘骁骞的采访意愿对接给贩毒集团,在等待了几个月之后,他得到了同意的回复,条件之一是,必须要打上足够的马赛克,不能透露任何可以被追击到的信息。
贩毒集团之所以答应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想向外展示自己所拥有的强大势力,毕竟这个中国记者就住在巴西,料想他也不敢耍花招。
2月的一个清晨,里约还没有从狂欢的宿醉中醒来,刘骁骞与线人一起,赶往约定的贫民窟。
在经过十多个由重机枪防守的关卡之后,刘骁骞被带到了一个不到20平米的房间。
后来,刘骁骞回忆进入这个房间的第一感受:“空气中粉末飞扬,掺杂着一屋子人的气味和声音,而几盏高瓦数的电灯泡将它转化为一股氤氲的热气。我的眼睛像是被人拿手电筒照过一样,突然有点看不清。”
彼时,随着世界杯临近,又恰逢狂欢节期间,毒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这个可卡因加工窝点也在加班赶工。
小小的房间里,一群人被分为3组,分别从事分包、封口和贴标的工作——
分包由贩毒集团中最资深的人负责,将三公斤的白色粉末分成独立包装,每一小包都是两克粉。
封口则相对简单,只需要将袋子打上两个活结,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刘骁骞在这里看到了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穿着卡通图案的黄背心,姿势却十分娴熟,显然不是新手。
毒品袋上的标签更是出人意料,上面印着价格、贩毒集团的名称、贫民窟的名称、贫民窟首领的标志,甚至还有毒贩支持的足球球队的徽章。
在标签的底部,还印着一句话:“如有质量问题,请到购买处申诉。”
刘骁骞拍摄的毒品与标签
刘骁骞在这个窝点待了30分钟,短暂,却险象环生。
过程中,每当他把摄像机拿出来,都会有一些人冲他吼:不要拍了。
快结束的时候,刘骁骞提出要录制一段现场出镜素材,来证明这些画面是自己实体探访所得。
但当他对着镜头说完中文的出镜词,负责人立刻上前,质问他到底说了什么。
事后,当他回到住处整理素材时,他听到在自己出镜的背景音中,有三声明显的枪响——贩毒集团内部的信号,生死就在一线之隔。
“没有比开工中的毒品加工窝点更容易遭到突袭的地方,每一秒的停留都要冒着极大的风险。无论是警方还是敌对的帮派,随时都有可能对这里发起进攻,而在一场枪林弹雨中,我们和在场的毒贩没有任何区别,生还的机会几乎为零。”后来,刘骁骞补充道。
而这一年,他仅仅26岁。
《走进“上帝之城”》专题片
2014年,由刘骁骞这次探访而得的专题片《走进“上帝之城”》在央视播出,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他淡定自若地行走在荷枪实弹之间,外表的斯文瘦弱与凶恶的贩毒分子形成鲜明对比,被网友戏称为“最强走基层”。
又因为嗓音偏向稚嫩温柔,他还得到了一个称号:“奶音猛男”。
在镜头里,他采访了一个路过的毒贩,问他:“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毒贩说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消防员,因为可以救人:“但我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个念头,像你看见的这样过着每一天。”
他扬了扬手里的枪:“在贫民窟,每天我们上床睡觉时,都不会想象明天,我们活在当下,不去思考未来。”
时间倒退回刘骁骞的童年,这样的未来,他似乎早有准备,却也意料之外。
1988年,他出生在福建泉州,在小学同学的口中,他是一个仅仅被打破了保温杯都会哭着跑回家的“胆小鬼”。
但接受采访的同学与老师对刘骁骞的记者身份都毫不意外。
自高中开始,在同学们的作文还局限于歌颂勇气与励志时,刘骁骞就已经在作文中“写抢板蓝根、抢盐等社会事件,批判国民劣根性”。
2006年,刘骁骞考进了中国传媒大学,学习葡萄牙语——这并不是他的第一选择。
彼时,他最想学的专业是西班牙语,但那一年,中国传媒大学并没有在福建招收该专业学生,他退而求其次,准备考德语。
但他又一想,福州、厦门这些大城市的学生可能比自己更有外语优势,最终在志愿一栏填报了葡萄牙语。
成绩出来后,他是全福建省所有报考中传的学生中成绩最好的,阴差阳错。
刘骁骞旧照
但选择没有如愿,不代表没有后续发力的机会。
大学期间,他兼职做翻译,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更是争取到了著名的体育电视网ESPN的奥运报道团,做采访联络人和翻译的工作。
四年之后,他从学校毕业,和许多大学生相同,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好奇。
恰好央视有一个驻巴西的外派记者岗位,他把握住了这次机会:2011年,23岁的刘骁骞成为了中央电视台拉美中心记者站记者。
自此,开始了他勇往直前的人生。
他在微博里写:“其实我啊,也很想去北欧,很想去荷兰,去中欧,再一次去法国,可是命中注定只能一直去亚马孙,然后带着各种雨林疾病回圣保罗(巴西城市)。”
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有一句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离现场越近,离真相就会越近,这也是刘骁骞始终秉持的职业准绳。
2014年,在里约的贫民窟,刘骁骞曾被邀请参与了一场葬礼。
葬礼的主人是18岁的亚历克斯,死亡原因是枪击。
他在凌晨骑摩托车回家,被巡逻的军警误以为是毒贩,警察随即开枪——不久前,亚历克斯刚刚被军队录取,葬礼的当天,正是他准备去军队报到的日子。
他的父亲控诉警察“为什么要朝头部开枪”,他的母亲也已经哭不出声,她试图向刘骁骞表达自己的悲伤,但声音已经嘶哑,每一个单词都像是被按在砂纸上摩擦过。
夜晚的贫民窟最为危险
不论外界将里约吹捧的多么光鲜,里约从来不是一个祥和的城市。
2014年,里约州政府安全厅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该州每10万人中就有42人死于凶杀,远远高于其他国际城市。
当社会秩序变得混乱,子弹往往比往常更加盲目。这些子弹来自毒贩,也来自保卫秩序的警察。
在里约贫民窟,死亡如影随形。
自搬到巴西之后,刘骁骞就一直计划着要记录下来里约贫民窟的清剿行动,却始终被里约政府搪塞推迟。
无奈之下,他干脆通过广播电台的公告,自己去追寻警察的痕迹。
某天早上,刘骁骞与摄像行驶在里约西区的道路上,突然听到广播里传来声音:“精英部队正在进入阿卡立贫民窟,现场传出交火声……”
他当机立断,前往冲突现场。
随后,他跟随着特警部队的车辆,到了警察局,找到局长,说明了身份与来意。
局长思索了片刻,默许了他们的拍摄。但局长一再强调这并不是“批准”,因此警方没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安全,“你想进就进吧,但生死不管”。
之后的镜头中,刘骁骞就穿着简单的防护装备,跟在警方身后,向中国的观众进行报道——
警方击毙了一名毒贩,刘骁骞慢条斯理地描述当前的画面:“毒贩大概是在半小时之前被警方击毙,大家看到,鲜血流出了好几米”。
他话锋一转:“刚才警察告诉我们,还需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他的同伴有可能在暗处,随时对我们发动进攻。”
刘骁骞(右)报道清剿现场
夜幕降临,刘骁骞先是跟随警方去到了一桩位于市中心的凶案现场,死者连中数枪,而根据现场遗留的弹壳等痕迹,凶器正是毒贩最常使用的口径为5.56毫米的狙击步枪。
现场刚刚清理完毕,警方又接到一桩凶案通知,案发现场正是被毒贩控制的一处贫民窟。
刘骁骞继续跟拍。
来到现场,刘骁骞看到一个25岁左右的年轻男性的尸体,脑部连中五枪,警察判断开枪距离小于1米,并在死后被人抛尸至此。
抛尸地点四面开阔,没有任何遮挡,突然,警察告诉他,毒贩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行动,“他们还知道你们在这里拍摄”。
一瞬间,刘骁骞明白了自己所处的情势,这也许正是毒贩所做的一个圈套:“毒贩看我们,就像看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一样”。
几分钟后,贫民窟内响起密集的鞭炮声与枪声——贩毒集团最后的警告。专案组决定立刻离开贫民窟,刘骁骞的拍摄,也被迫停止。
这些残酷、真实也珍贵的镜头陆续地在电视上播报,这也不过是刘骁骞数千个拍摄日里,再普通不过的一天。
总有人问刘骁骞,为什么要主动将自己放置在危险之中,就不害怕吗?
刘骁骞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一句话回答:
“由于缺乏想象力,所以我被保护得很好。”
刘骁骞的拍摄“意外频发”
事实上,为了看到世界的真相,刘骁骞总在撕破想象的空间。
2016年,28岁的刘骁骞来到了哥伦比亚。
恰逢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以下简称“哥武”)准备签署和平协议,刘骁骞有了一个新的选题:探访“哥武”丛林游击队的营地。
“哥武”成立于1964年,是西半球最古老的反政府武装组织,也是哥伦比亚境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完善的武装组织。
可以说这次探访,危险程度与深入贩毒集团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骁骞在“哥武”营地(下同)
在长达数月的接触和申请之后,“哥武”的最高指挥部门批准了他们的采访。
但直到采访的前一天,他们也没被告知营地的具体位置,只知道要先去哥伦比亚西南部的考卡省。
考卡省是“哥武”的地盘,但同样也有包括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以下简称“哥解”)在内的其他阵营的武装力量。
可以说,仅仅取得“哥武”的同意,并不能保证这一路上的畅通无阻。
就在一个月前,一位西班牙的女记者在内陆地区采访时,就被“哥解”绑架,另外两名前往报道绑架事件的记者,也遭到劫持。
“这里是媒体的禁区。”刘骁骞说。
出发的当天,刘骁骞特意把住处收拾了一番。
“如果被绑架了,或者出了什么意外,别人来我家调查或者退房,不会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不整洁。”
毕竟,除了暗藏的危机,“哥武”本身也是以绑架人质著名的:过去的40多年里,他们共绑架了10583个人质。
他从住处出发,被一波接一波的人带着,换乘了不同的交通工具,在下午四点左右,抵达了约定的村落,等待了大概四个小时之后,才有两个穿着便衣的游击队员前来与他交谈。
他们问刘骁骞,这次想来拍什么内容,用作什么用途。尽管之前,刘骁骞已经将自己的拍摄计划原原本本地告知了“哥武”最高领导人。
因为天色已晚,所以当晚他被指定在一所民居过夜。直到第三天,他才被安排上一辆车,“在接力赛般的旅途的终点,抵达了‘哥武’的营地”。
他也是近年来唯一在哥伦比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的停火协议生效前进入“哥武”控制区的亚洲记者。
他离真相更近了一步,也与地狱咫尺之间。
“哥武”被称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更是哥伦比亚当地许多毒贩的庇护者,每年仅从毒品贸易中,就能获利数亿美元。
刘骁骞描述了一个细节。
在“哥武”营地,不管是十八岁的少年,还是二十岁出头的少女,手里拿着的都是狙击步枪等重型武器——在贩毒集团,一般只有中高层才会被配备重型武器,底层人员顶多是轻型的左轮手枪。
刘骁骞在这个营地内生活了三天,没有手机信号,唯一能和外界联系的卫星电话也被“哥武”暂扣。
第一天晚上,政府军的战机就盘旋在这个营地上空,“哥武”的游击队员后来告诉他,他们在那个夜晚穿上了防弹衣,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彼时,“哥武”已经有几百个营地在顷刻间被投下炸弹、变成火海,甚至连“哥武”最高领导人之一的阿隆索·卡纳,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在2011年被夺走生命。
刘骁骞(中间黑衣服)在“哥武”营地合照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刘骁骞的到来竟然给这个营地带来了些许安全感。
第二天起床后,一位游击队员对刘骁骞说:“你们是记者,还是其他国家的,你们的安全应该是有保障的,而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刘骁骞只好告诉她:“可是哥伦比亚政府,恐怕不知道我在这里。”
直到刘骁骞回到家里,他才知道游击队员这句话或许还有深层含义——2002年,“哥武”与哥伦比亚政府谈判破裂,随后,“哥武”就绑架了当时哥伦比亚的前总统候选人。
在这位候选人的自传中,他写道,当时“哥武”的绑架动机就是“营地内有一个外人就会比较安全”。
事实上,在“哥武”营地的每一刻,恐慌都始终笼罩在刘骁骞的心头,只是当摄像机的镜头打开,记者的职责迫使他必须专业地完成采访。
他在微博里写:“在营地里的那些黑夜,和游击队员睡在一起的我,只要眼睛一闭上,就浮现出那些被绑架了好几年,或者再也没有活着出来的人的脸。他们也曾经像这样睡在丛林中。”
在哥伦比亚,刘骁骞以身犯险的,也不仅仅只有这一个瞬间。
2018年,刘骁骞带着他的镜头,来到了麦德林——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城市被臭名昭著的贩毒集团控制,是全美洲的可卡因走私中心,有“可卡因之都”的称号。
几经周折,刘骁骞与当地一家制毒工厂取得联系,被允许探访一处位于安第斯山深处的可卡因生产窝点。
他采访了种植古柯叶(从中提取的古柯液是制作可卡因的原料)的农民,对话了正在搅拌液体的制毒工人。
他坐在生产古柯膏(古柯膏再加工就可以变成可卡因)的“实验室”内,没有佩戴任何保护面具,淡定地介绍自己的感受:“现场有一股非常刺鼻的气味,因为除了古柯叶原有的汁液味道之外,他们还放了大量的化学药品进行发酵,在现场,不管是眼睛还是喉咙都能够感觉到刺激。”
刘骁骞在实验室内
面前是制毒工人在添加化学药剂
哪怕这里流传着一句话:“每一公斤可卡因,可以夺走6条人命。”
而刘骁骞就抱着2.27公斤重的古柯膏,给观众介绍这些膏体的形状、味道,仿佛怀里的是家常豆腐一般,但这些洁白的膏体却代表着罪恶、权欲与痛苦,“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可以卖到6万美金。”
可以让人倾家荡产,陷入地狱。
在拉美地区,很多次报道都是刘骁骞与死神在生死线上的交手。
这期间,有毒贩的恐吓、枪支的威胁,有诡异莫测的雨林毒物,还有数不清的丛林疾病。
但他似乎并没有世人想象中的咬牙苦撑,他说:
“每一个调查报道都犹如亚马孙河系大大小小的支流,地貌迥然,有各自的风光和险阻。我既希望旅途尽快结束,又期盼旅途尽早开始。”
2019年,这趟旅途,转向美国。
结束了整整9年的驻巴西记者生活之后,31岁的刘骁骞被调往美国,去发现这片大陆上发生的故事。
危机依然四伏。
有时他在旧金山。
镜头里,刘骁骞用手指着吸毒者刚刚注射完毒品的针筒,在他身后的不远处,就是处于毒品影响状态下的无家可归的吸毒者。
在无家可归问题最严重的天德隆区,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帐篷与吸毒物品,商家甚至在对着流浪汉喷洒消毒水。行走在这样的街道,刘骁骞都不敢把鞋子穿回到酒店。
他说:“这样的场景正在吞食旧金山的街头。”
刘骁骞拍摄的旧金山街头
有时他在芝加哥。
在被称为“血腥劳动节周末”的夜晚,几乎每小时都有枪击事件发生。
他跟着警察的脚步,发掘着隐藏在冰冷的死亡人数背后的犯罪现场。期间,连值班警察都劝告他“尽量离危险远一点”。
刘骁骞拍摄的芝加哥“血腥周末”
2020年5月25号,明尼阿波利斯市一位黑人男子被警察“跪死”一案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流传出的视频中,这位姓氏为弗洛伊德的男子被警察从车上拉下来,戴上手铐,盘问了两分钟。因为他拒绝上警车,警察将他摁倒在地,用膝盖压住他的脖子,长达8分46秒。
他反复说着“我无法呼吸”,直至死亡。
该事件引起了美国当地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冲突愈演愈烈,示威者点燃了警局,与警察产生了数次冲突。
30日,刘骁骞抵达了明尼阿波利斯,此时,抗议活动所造成的火灾甚至还没有完全平息。
而就在一天前,美国CNN电视台去往抗议现场直播的记者被当地警察逮捕,警方的说法是:报道团队没有听从警方指挥。
刘骁骞在明尼阿波利斯当地报道
警察在驱赶人群
7月份,他又赶往波特兰进行当地抗议活动的报道。镜头前,他介绍着当下的情景,身后就是警方不断投掷的防爆弹。
刘骁骞在波特兰
一个月后,美国威斯康星州有一个非洲裔男子布雷克遭警察枪击身亡,冲突进一步升级。
在抗议活动现场,布雷克的父亲询问了刘骁骞的身份,得知他来自中国后,对他说:“你可以问我问题。”
刘骁骞曾说:“外人很难想象中国驻美媒体报道环境多么艰难。特别是在大型抗议风暴眼里说出‘中国’的时候,我已经做好被辱骂和驱赶的准备。那一瞬间的紧张比当年采访毒贩难多了。”
“我愿意接受中国媒体采访”
在美国,刘骁骞不仅要深入危险地区探访,当他褪下媒体的身份,他依旧要面临数不清的偏见与莫名其妙的攻击。
2020年,他戴着口罩从芝加哥的临时住所出来,迎面走来一个没有戴口罩的白人。
对方用手挡在嘴上,对他叫嚣:“你看我也戴着口罩。”
刘骁骞没有理会他,于是对方变本加厉,发来了一连串肮脏的咒骂——这样的事情,在短短半个月时间里,发生了三次。
更让他感到诧异的是,当他将自己的遭遇讲给白人朋友们听时,朋友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怎么判断是因为你是亚裔才对你做的呢,也许他那天只是心情不好罢了。”
偏见,谩骂,隐瞒,驱逐。
2020年,美国驱逐了60名中国记者,刘骁骞直到签证到期的最后一天,才收到了美国的续签通知。
他说:“我真的好久好久不敢买一袋完整的大米,因为说不定下一周就要撤回国。”
2022年12月,34岁的刘骁骞被央视评为“十佳记者”,如今,他又出现在俄亥俄州,报道着脱轨火车的最新进展。
在该条报道的视频底下,有一条评论被顶上了前列:“社会是屋,新闻是灯,记者是油。”
油在燃烧,社会的光就不会灭。
诚然,刘骁骞看上去与“高大威猛”并不沾边。
他喜欢毛茸茸的动物,不喜欢被晒,每次出外景都会戴一顶遮阳的帽子,出镜的时候再把帽子摘下来。
他收集了许多印着有趣图文的口罩,也会把坐飞机时分到的消毒纸巾收起来再利用,在看到他的脸之前,甚至很多观众根据声音判断他是个女记者。
可是,谁又能质疑他身体里蓬勃而出的勇气与力量呢?
为了报道本身的价值,为了揭露世界的不同切面,他行走在不同的国家与城市,几乎每隔几年就要更换一次关系网。
他很难交到知心的朋友,却与危险并肩前行。
他选择将真相摊开放在观众眼前,却也不得不与死亡和暴力如影相伴。
只是,当那些赞美与敬佩的声音传到刘骁骞耳中,他摆了摆手,露出斯文俊秀的笑,他说:
“全球的海外央视记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用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把世界带给中国。”
仅此而已。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