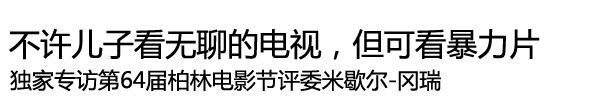

导演兼评委米歇尔-冈瑞在玻柏林接受凤凰娱乐专访
凤凰网娱乐讯 柏林当地时间2月9日,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之一、法国导演米歇尔-冈瑞接受凤凰娱乐独家专访。按照大会规定,评委按理不会接受访问,不过冈瑞的新作《高个男人快乐吗?》恰好入围了本届电影节全景单元,这位忙里偷闲的评委也正好向媒体详解自己的新片。
《高个男人快乐吗?》是一部纠结于语义和哲学的粉丝电影。身为法国人的米歇尔-冈瑞,跑到纽约,找到自己的学术偶像诺姆-乔姆斯基进行采访,并一笔一划将自己与这位语言学家的讨教过程制作成一部动画纪录片。对自然科学极其感兴趣的冈瑞,开始以自己熟悉的影像媒介,去深入浅出的解析影响人类认知能力的复杂概念。
譬如,在一栋矮小的屋子里住着一个高个男人,那么他能快乐吗?乔姆斯基向这个好学的法国人讲解着谓语变化的秘密,Is the Man Who Is Tall Happy?导演将单词打乱后再以搭积木的手绘画面拼接。
在接受凤凰娱乐专访时,冈瑞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至少他的偶像乔姆斯基挺满意。不过这段呆在柏林的时间,可没时间多想宇宙和物理问题,评委会的工作压力不小,得不自在的看很多电影。
谈动画:一张纸一支笔搞定的科教片
凤凰娱乐:你怎么产生拍这样一部“科教纪录动画片”的念头?
米歇尔-冈瑞:制作一部科学纪录片一直是我的梦想。我很少看电视,但一旦拧开,总爱去瞧一些关于黑洞、宇宙、物理学和数学的冷门节目,但它们在视觉表现上并不怎么样,经常会过于夸张而产生欺骗性误导。所以我决定自己也来尝试做一部。
凤凰娱乐:如今的动画手段和工具往往都很复杂,你怎么想到用这么简笔画的方式?
米歇尔-冈瑞:因为我的初衷就很简单,就是记录与乔姆斯基聊天的过程。一张纸一只笔就够我记下关键点了,那么不如干脆把纸上的涂鸦生动起来。压根就没想过用橡皮、玻璃什么的人偶手段或是我以往拍摄音乐录影带所擅长的停格手段。
谈乔姆斯基:为公众打开认知语言学家之门
凤凰娱乐:作为电影人,你有哪些阐释乔姆斯基学术理念的优势?
米歇尔-冈瑞:我尽量利用自己在动画方面的技巧和能力吧,相较文本,图形的方式能让我更容易理解乔姆斯基的思想内容,尤其是那些儿童与生俱来的普遍语法概念,桌子、椅子、杯子,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普遍语法,我开始乐于将它们解构后再以动画重构。
凤凰娱乐:乔姆斯基看过此片了吗?他喜欢吗?
米歇尔-冈瑞:看过了,非常喜欢。他之前担心的误读并没发生,反倒觉得动画很忠于自己的思想。
凤凰娱乐:访谈中的哪一部分最打动你?
米歇尔-冈瑞:当他谈及自己儿时最初记忆,以及与妻子的关系时,都很打动我。但还是当我意识到自己终于进入他哲学世界那一刻最为高兴。作为解释媒介的电影确实有着误读的可能性,但我们对话的明确主题或许起着挽救作用吧。
凤凰娱乐:乔姆斯基对你的人生有着重要影响吧?
米歇尔-冈瑞:不止是我,我觉得他的思想对整个人类历史都是至关重要的。很幸运我能见上他并与其深聊,作为一个活跃左派知识分子,他对美国爱之深责之切的态度也影响着我。
凤凰娱乐:这么样的特别制作方式,是否也有利于向大众推荐乔姆斯基的思想呢?
米歇尔-冈瑞:我想是这样的。他的著作当然很复杂有时甚至还很说教,我也很为挑选哪些内容和他交谈而犯愁。如今这样的动画组织方式是还不错,但也有着过于简化的危险倾向,过简会让观众产生误读,毕竟他那些理论概念始终还是很复杂的。不过动画手段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公众打开一扇通往枯燥语言学的大门,让有心人想去探寻更多。我既不想胡乱解构理论,也无力去进行更多深入,走一步算一步吧。
凤凰娱乐:可你更为人熟知的角色,是一位有着匪夷所思绚烂影像作品的超现实主义导演,而乔姆斯基是一位热衷于现实政治的行动主义者。
米歇尔-冈瑞:行动主义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总竭力而为渴望改造世界。但他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反倒是真正激发我影像灵感的部分。可能与大众对我的认识不同,很多时候,是科学纪录片更让我能进入做梦状态,并开拓我的创作视野,而如今去凝听他人古怪的梦境,反倒容易打扰我。
12 |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