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演娄烨在内地文青中一直都很有市场,这次携金马六项大奖之威冲击贺岁档,意图在票房上有所突破。但影片的题材、拍摄手法等依旧不那么主流,是否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尚且是个未知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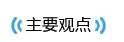

《推拿》就是娄烨自己的“超级大片”
嘉宾:
正方:
卡卡西北偏北:资深电影记者、影评人
反方:
灰狼:影评人,电影学博士
剧情简介:
这是一个发生在盲人按摩中心男女技师们之间的爱情故事。
这里有一个风流外向、能吟诗跳舞的盲人老板沙复明(秦昊饰),也有经常被顾客赞叹其美貌的“会所之花”都红(梅婷饰),还有整天沉浸于自己精神世界里的“小正太”小马(黄轩饰),以及热恋中的刚从外地投奔沙老板而来的王大夫(郭晓冬饰)与小孔(张磊饰),还有公认的“开心果”、多才多艺爱洗头的技师张一光(穆怀鹏饰),以及隔壁洗头房美丽温柔的发廊妹小蛮(黄璐饰)等,生活各自精彩,人们彼此相安。然而正是“嫂子”小孔身上特有的女人气味突然唤醒了小马对爱的渴望,不断念着“嫂子”的他不经意转动了命运之轮,使得整个推拿中心各个盲男盲女技师们之间的爱情与生活发生了激烈又动人的转变……
《推拿》:从小情怀到大众通感的影像实验
文/卡卡西北偏北
通过第八部电影《推拿》,导演娄烨终于实现了两个突破:第一个突破是他终于对拍“别人”的故事有了兴趣——是有真实社会属性的“别人”、与娄烨生活没有交集的别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所有角色都是其个人审美的延伸。第二个突破是他终于不再同情自己的角色——是那“我尊重你”的不同情。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女主角一边在KTV里唱“他们在哪里啊?他们都老了吧?”,一边哭出鼻涕。两个突破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即娄烨从那种无谓的对疼痛感的迷恋里走出来了。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前几部电影里总会有做爱场面,做爱时女主角总在哭(也不知道为啥做爱那么痛苦),《推拿》里也有不少做爱场面,但是谁也没哭。
它当然也有疼痛感。比如王大夫挥刀自残、小马用碗碴抹脖子、都红被扎断的手指,沙复明喷出的一口鲜血……但这些痛感是强加在观众心灵上的,而不是施予角色的。导演(与摄影师曾剑)用纯技术的方式,完成了从小情怀到大众通感的影像实验。
该实验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有人朗诵片名、演职人名单,剧情重要转折等也有无情感的旁白辅助,让盲人也能听懂电影;其次是几场重头戏都用夸张的影像处理,让不盲的人看不清。套用影评旁白,“在盲人的世界里,他们认为能看得见的人是另外一种生物”。《推拿》所做到的,起码在姿态上,是把两种生物同等对待。
华彩的段落莫过于小马失而复明的十几分钟:画面让人无法喘息,光源时有时无;调色夸张;无目的地晃动与剪切;特效做出移轴效果,焦点游移、景深关系凌乱;期间伴随着同样混乱、丰富的音效。有那么一两分钟,观众会误认为它是小马的主观视角,但小马很快入画,这依然是强加给观众的“主观视角”!从传播的角度讲,这十几分钟观众接收到的信息一句话就能概括:小马复明啦!——显得冗余。可情绪上讲,这十几分钟不是为了让观众理解或同情盲人,而是让观众变成盲人——胜过千言万语。
展现“盲”对所有导演都是难题。最俗套的莫过于《黑客帝国3》与《超胆侠》,前者已成仙,尼奥看不见人,但能看见一团跳动的二进制编码;后者耳朵比蝙蝠还好,听到雨水打在女主角脸上,就在脑海里勾勒出了她的轮廓,嗯,可以做老婆的女人。又或者像《闻香识女人》那样,帕西诺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灵敏的鼻子。同类题材,好莱坞永远会通过强化主角的“神性”来实现“看见”。他们何止不盲,就差开天眼了。两相比较,您就能明白《推拿》反其道而行之的价值了。
不同于贾樟柯导演对提炼社会符号的偏好,娄烨导演其实一直是个“技术控”。《苏州河》、《颐和园》里随性的跳轴剪辑,《浮城谜事》中的长镜头都是例证,我们之所以习惯性忽视他的特点,是因为那些都是文艺片,没有泛好莱坞化的精致。这些技术花招,有时反而变成大家吐槽其“个人化”的靶子。《推拿》不同,它的手段越炫酷,就越让观众接近应该体验的真相。所以与其说是娄烨找到了表现“盲”的好方法,还不如说娄烨对视觉花招的迷恋刚好与《推拿》相得益彰。套用凤凰电影主编法兰西胶片的话说,这就是娄烨自己的“超级大片”。
我们也可以把本片与挪威电影《盲视》放在一起看。后者把更多功夫花在了对盲人心态的刻画上:女主角宅在家中,幻想老公欺负她是个瞎子,天天在外面滚床单。诸如此类的情节越琢磨越像那么回事儿,以至于她分不清现实与臆想,心也盲掉了。两部片子着力点不同,都值得赞赏。
然而《推拿》的“通感实验”是不是过于压迫性了呢?只做展现算不算故弄玄虚?会不会缺少“人文关怀”呢?于是技术问题最终还是变成了“世界观”问题。
其实哪怕在原著小说中,毕飞宇也没有把这群推拿师作为完全的弱势群体来写。很多盲人之间的龃龉与冲突,并未出现在电影中。弱势群体作为宾语,最常用的谓语就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是个带着从上到下姿态的动作,我们觉得自己有别人所没有的,才能愿意弯下腰“人文关怀”一下。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假设我是盲人,看到了一部“盲人真可怜”的电影,应该也挺烦的。如王大夫切腹前所说:“你在大街上见过讨饭的盲人吗?我们是要脸的”。作为盲人,我未必比你卑微,你也不能要求我比你有更少的欲望,或者有更美的心灵。我与你一样,不管我看不看得见。恕我重复,“盲”的通感体验,才是《推拿》最重要的价值。
影评结尾讲段子是非常业余的表现,但还是忍不住:笔者多年前经过大望路,有个盲人来求助。为了送他到目的地,我们必须跨过那条双向12车道的路口。开始时我拉他的手,走得很慢。眼看着信号灯上的绿色一寸寸消逝,我对他说,要变灯了,我们得快点走。听完我的话,他拽着我的袖子,健步如飞。我一路小跑,跟着他到了对岸。那一瞬间,我既没觉得帮助他是值得赞美的事,也没觉得他求助我是件添麻烦的事。我觉得这位盲人就是活在《推拿》里的角色,他的行为就是《推拿》的注脚。

导演娄烨所谓的“怜悯”是一种伪装
《推拿》:别拿盲人求怜悯
文/灰狼
很多人眼里的娄烨是一个革命者,但他电影里的人物都是可怜人,如《苏州河》里的美人鱼表演者、《颐和园》里的学生、《春晚》里的同性恋者、《花》里自由主义的婊子以及《浮城谜事》破碎的家庭。《推拿》里是一个按摩院里的盲人集体,典型的弱势群体,这些可怜人的身份映射着戏外的导演——他是中国审查制度的受害者。
革命的背后是求怜悯的姿态,娄烨用这双重的姿态收获了自己的信徒。这一届金马奖在面对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下给《推拿》最大的荣誉,在某种程度上是台湾方的一种消极的抵抗,在这种抵抗的话语中,他们忽视了《白日焰火》,却肯定了《黄金时代》,这是实实在在的“乱局”。所以《推拿》在整个大形势下,是沾了意识形态的光。
倘若说《推拿》好在哪里,恐怕很少人能做出具体而深刻的表述,最后仍是落到大而无当的“社会关怀”、“温情”一类的空洞字眼。《推拿》的电影文本其实是一种“偷窥”视角的延伸,在这个图景里,每个盲人都做着掩耳盗铃的游戏,观众则躲在黑暗里,见证着这一群居而产生的扭曲。它体现了物以类聚的结果,一群盲人在一起遭遇的道德“陷落”的过程,在这个群体里,眼盲成为盲人向现实抵赖的工具,黄轩扮演的小马肆意地侮辱“嫂子”,便是这种“抵赖”的直接表征。这是“审丑”的呈现,在电影开头对准一张张脸孔的特写中,是广角下的扭曲效应,这种“审丑”构成了娄烨对这个群体的视点。
这也意味着娄烨所谓的“怜悯”是一种伪装,用这种伪装来迎合现实的伪装——正常人对盲人群体的伪装。它利用了人的虚伪,利用了观众面对文本的“慈悲”,于是娄烨的“怜悯”仅仅是一种话语的工具。但在毕飞宇的小说中,这种怜悯是实存的,毕飞宇所建构的两个极度相似的群体:盲人按摩师和妓女(按摩女)得到了表达,但在电影在小马和小蛮身上表述更多的是一种相互的消费、欲望的排解,而非同病相怜。对盲人不健康心理状态的描写,是整个电影里被放大的部分,发展成王大夫切腹和小马打人的暴力行动。《推拿》所建构的盲人生态结构是娄烨用电影呈现的病理学研究,虽然它的表述真实而又犀利,但它并非是一种社会大爱的书写——将之理解成这样,也是自欺欺人的解读方式。
电影里代表美的是都红,她盲掉的双目,似乎仍然晶莹剔透,却体现了审美的无力。沙复明是盲人中的文艺青年,他可以说诗情画意的句子,却不能分辨对面的姑娘是个猪扒。娄烨的荒诞,犹如伤口撒盐一样涂抹在这些人物的伤口,并令沙复明一样的人物吐出一口狗血。在这样的场景中,悲天悯人已经全部被消解,所有的一切都沦为诱发的工具。
“怜悯”是道德的产物,而不是革命实用主义,在反意识形态的话语中植入的概念,已经丧失自己纯真的意义。娄烨的电影语言则是丑的,也是粗糙的,它在这个年代愈发精致化的同时反其道而行,这种姿态,好听点叫“坚守”,难听点叫“作秀”。娄烨的好处是处在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国人思想压抑的时代,在这样的大时代里,那种有着反叛意识的社会活动者最容易得到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的认可,文本本身的价值则让位次席。

这是一个发生在盲人按摩中心男女技师们之间的爱情故事。该片聚焦盲人推拿师这一特殊群体,展现他们的喜怒哀乐。
策划:凤凰电影组
撰稿:卡卡西北偏北、灰狼
责编:法兰西胶片、扭腰客、芥末蘸酱
监制:刘帆 李厦
出品:凤凰网娱乐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