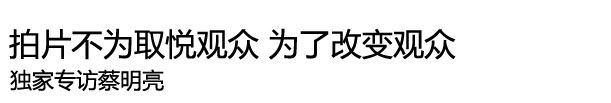
请先确认是否安装了 最新Flash 播放器
请点击安装按钮
安装
蔡明亮接受凤凰娱乐的独家专访
凤凰网娱乐讯 意大利当地时间9月5日,第70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竞赛片、蔡明亮执导的《郊游》进行官方首映,蔡明亮携主演李康生、陆弈静以及两位小演员到场。随后,导演蔡明亮接受凤凰娱乐独家专访。
蔡明亮的投资人曾说,他的作品总会留在电影的历史里。在国内电影业喧嚣不已之时,回过头来与蔡明亮对话,无疑能让人冷静下来,感受电影的原生态创作力量。
这部新片《郊游》,选在台中秘境拍摄,此处是东区台糖大水池,当年开发案中止,荒废多时形成自然湖泊与生态,还有高大树群,成为蔡明亮眼中不受拘束的“郊游”秘境。而他的老班底李康生、陆弈静、杨贵媚、陈湘琪也齐集出演此片,正如他所言,《郊游》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片,与自己最喜欢的这些演员合作之后,似乎就可以心满意足地挂印了。
对于蔡明亮的逆市而行,媒体与他争论过多次,但他依然固我,“不为观众拍片不是为了丢掉他们,而是为了改变他们”,他自信自己20年来的十部长片,每部都是杰作,“它们都被讨论,有时候被学生研究。如果你一直被看到,一直在不同的地方被使用,它是扩散式的,而且首先是延长的,它不是消费品,消费完就没了”。
【对话实录】
李康生是我电影的特别意义
凤凰娱乐:拍摄“人肉招牌”的由来是什么?
蔡明亮:这个行业一直存在你的生活里,在全世界都有,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在台北街头看到时,很震撼,当时就很想找李康生来演这个人物,他也很像这个人,没想到十几年后有这个机会。
凤凰娱乐:和您合作多年的这些人对您的意义是什么?
蔡明亮:和我工作的人都合作非常久,比如我的摄影师也是从第一部电影到现在,我觉得不能没有他们。第一次与李康生合作时,他让学戏剧的我重新反省表演到底是什么,经过20年的时间,我觉得,他是用20年的时间来吃那颗高丽菜的,那不是单纯的表演和演技,那样做不到那个状态,李康生几乎就是我影片的一个特别的意义,用摄影机关照着,从他的青春逐渐到变老,这是很有思想的一个命题。生命很短暂,有一群人愿意陪我很慢地走这条电影路,我非常感谢他们。
慢很美,就像老也很美
凤凰娱乐:为什么您的长镜头要用这么长时间?
蔡明亮:关于长镜头,快慢不是什么问题,我遇到很慢的李康生,所以我就开始慢,有时候觉得不够慢,他现实里更慢,而且我老了我也快不了,慢很美,就像老也很美。创作都是在处理每个人生的不同阶段的感受和领悟,然后表达出来,所以快不了。
我其实很迷惑,为什么要快,为什么电影要90分钟?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的节奏,那样的表演?我是不停通过创作来寻找我迷惑的出入,慢是我其中的一个手段。
我觉得观众可能会慢慢不习惯看美式的电影,他们不见得常常看到慢的电影。
人家老是跟我说,你电影为什么慢,慢我不觉得,对我来说不是个话题,没什么好讲的,就是我慢,你们快,为什么你们非要讨论慢呢?我觉得我们是照着本色在做,自己的性格、状态在创作。
凤凰娱乐:因为你刚刚说到慢的问题,其实你在这个电影里面,有的时候会调节观众的心理时间,比如说两个人在看画,好像有点像看展览,你是在调整到你看展览的那种心理时间。
蔡明亮:我觉得我后来的电影就越来越自由了,自由到说,我让一个法国人唱华语歌,虽然电影追求真实,但它毕竟是一个电影的世界,不是真的世界,是创作人的创造经营,利用它来表达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它可以有非常大的自由,要不然不需要有作者论。
所以我到后期,我的自由度是,我也很偏向于创作更纯的电影,希望观众有一天不见得在戏院在电影,他很可能是在一个美术馆看电影。那是可以变成一个展览的概念,所以壁画也好,演员的姿态也好,时间也好。在我其实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的时候,我先意识到,电影不可以被困住,不可以被戏院这个系统,被商业这个系统,被观众的习惯困住。所以我就拍了一个《不散》,《不散》之后美术馆又来找我了,开始跟我招手。

蔡明亮接受凤凰娱乐的独家专访
凤凰网娱乐讯 意大利当地时间9月5日,第70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竞赛片、蔡明亮执导的《郊游》进行官方首映,蔡明亮携主演李康生、陆弈静以及两位小演员到场。随后,导演蔡明亮接受凤凰娱乐独家专访。
蔡明亮的投资人曾说,他的作品总会留在电影的历史里。在国内电影业喧嚣不已之时,回过头来与蔡明亮对话,无疑能让人冷静下来,感受电影的原生态创作力量。
这部新片《郊游》,选在台中秘境拍摄,此处是东区台糖大水池,当年开发案中止,荒废多时形成自然湖泊与生态,还有高大树群,成为蔡明亮眼中不受拘束的“郊游”秘境。而他的老班底李康生、陆弈静、杨贵媚、陈湘琪也齐集出演此片,正如他所言,《郊游》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片,与自己最喜欢的这些演员合作之后,似乎就可以心满意足地挂印了。
对于蔡明亮的逆市而行,媒体与他争论过多次,但他依然固我,“不为观众拍片不是为了丢掉他们,而是为了改变他们”,他自信自己20年来的十部长片,每部都是杰作,“它们都被讨论,有时候被学生研究。如果你一直被看到,一直在不同的地方被使用,它是扩散式的,而且首先是延长的,它不是消费品,消费完就没了”。
【对话实录】
李康生是我电影的特别意义
凤凰娱乐:拍摄“人肉招牌”的由来是什么?
蔡明亮:这个行业一直存在你的生活里,在全世界都有,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在台北街头看到时,很震撼,当时就很想找李康生来演这个人物,他也很像这个人,没想到十几年后有这个机会。
凤凰娱乐:和您合作多年的这些人对您的意义是什么?
蔡明亮:和我工作的人都合作非常久,比如我的摄影师也是从第一部电影到现在,我觉得不能没有他们。第一次与李康生合作时,他让学戏剧的我重新反省表演到底是什么,经过20年的时间,我觉得,他是用20年的时间来吃那颗高丽菜的,那不是单纯的表演和演技,那样做不到那个状态,李康生几乎就是我影片的一个特别的意义,用摄影机关照着,从他的青春逐渐到变老,这是很有思想的一个命题。生命很短暂,有一群人愿意陪我很慢地走这条电影路,我非常感谢他们。
慢很美,就像老也很美
凤凰娱乐:为什么您的长镜头要用这么长时间?
蔡明亮:关于长镜头,快慢不是什么问题,我遇到很慢的李康生,所以我就开始慢,有时候觉得不够慢,他现实里更慢,而且我老了我也快不了,慢很美,就像老也很美。创作都是在处理每个人生的不同阶段的感受和领悟,然后表达出来,所以快不了。
我其实很迷惑,为什么要快,为什么电影要90分钟?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的节奏,那样的表演?我是不停通过创作来寻找我迷惑的出入,慢是我其中的一个手段。
我觉得观众可能会慢慢不习惯看美式的电影,他们不见得常常看到慢的电影。
人家老是跟我说,你电影为什么慢,慢我不觉得,对我来说不是个话题,没什么好讲的,就是我慢,你们快,为什么你们非要讨论慢呢?我觉得我们是照着本色在做,自己的性格、状态在创作。
凤凰娱乐:因为你刚刚说到慢的问题,其实你在这个电影里面,有的时候会调节观众的心理时间,比如说两个人在看画,好像有点像看展览,你是在调整到你看展览的那种心理时间。
蔡明亮:我觉得我后来的电影就越来越自由了,自由到说,我让一个法国人唱华语歌,虽然电影追求真实,但它毕竟是一个电影的世界,不是真的世界,是创作人的创造经营,利用它来表达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它可以有非常大的自由,要不然不需要有作者论。
所以我到后期,我的自由度是,我也很偏向于创作更纯的电影,希望观众有一天不见得在戏院在电影,他很可能是在一个美术馆看电影。那是可以变成一个展览的概念,所以壁画也好,演员的姿态也好,时间也好。在我其实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的时候,我先意识到,电影不可以被困住,不可以被戏院这个系统,被商业这个系统,被观众的习惯困住。所以我就拍了一个《不散》,《不散》之后美术馆又来找我了,开始跟我招手。

电影《郊游》海报
最后一部长片?因为很满足,20年十部长片,每一部都是杰作
凤凰娱乐:您为什么说《郊游》是您最后一部电影?
蔡明亮:主要是我身体不好,以前我就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兴致拍所谓的剧情片。我对电影的理解或者向往,可能逐步逐步在改变,我甚至在很多年前就觉得,拍电影干嘛?一百分钟干嘛?也许可以两分钟,也许可以5小时,但是大家都很害怕这种论调,因为你回到市场的概念,你就是有一个机制,电影院一天放六场,你懂我的意思吗?
尤其现在的电影发展越来越商业,好不好不重要,最重要卖钱,我们这种电影不是,你看得出来不是做生意的概念,真的想要纯创作,你说要不要生存,希不希望他卖座,为什么不呢?都希望大家来看。所以这种心理长期下来,在加上的确我觉得自己拍电影比一般人还累,累在哪里?累在手工。
它不是一个工艺片或者是一个画,画完就算了,它好复杂,一个东西要搞很久,从要钱,找钱,到真的拍,拍是最辛苦的,你心里想的是一个好作品的概念,可是有那么多客观的原因,资金、演员的挡期、工作人员等等等等。
到后来,我跟你讲,我拍电影是连银幕上的中文字幕,连片头片尾的字幕都是我打的,因为每一个都是节奏的问题。不是说没有人帮我做,他们没有办法帮我决定,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到后来你就知道,包括像卖票,在台湾,要宣传什么,你喜欢不喜欢都得去。
我后来觉得说,做电影,像做到我这种程度是非常辛苦的,当然我有我的快乐,我的快乐就是,比如说刚才那一刹那,作品完了大家鼓掌,我的快乐也许是跟我喜欢的工作人员、演员一起工作,可是长期下来我身体也不好,所以我不是说放弃电影,我没有要放弃电影,我只是说不想拍长电影,不拍应戏院那个系统要求的电影,我累了,我觉得腻了。
我希望“这是我最后一部电影的说法”变成真的,我很满足,我20年做了十部长片,每一部我都觉得是杰作,都被讨论,甚至有时候被学生研究,如果你一直被看到,一直在不同的地方被使用,它是扩散式的,而且首先是延长的,它不是消费品,消费完就没了,我觉得对一个电影创造人太奢侈了,因为一般人没有我这样的状况。
但我也相信命运,不知道会怎么安排我。我四年未拍长片,但其实一直在做短片的创作,我找寻的出路不是为市场和观众消费去拍电影,那样太捆绑我的创作。我没有浪费过我任何一次电影的机会。
凤凰娱乐:所以您还是有可能再拍的。
蔡明亮:我会拍影像,我自己一直在强调一个概念,我希望电影或者影像的创作,不是那么自私化,观众也不是要那么自私化地看这些东西,他可以在不同的场地去看,去使用他,所以我这几年没有间断地在做影像创作,我都视他为拍电影,我拍一个短片《行者》,对我来说也是电影。
只是媒介可能换了,好像这个电影也是用数码摄像机拍的。艺术片什么,对我来说都不重要的,有钱也不见得拍得好,没钱可能自由一点,所以我后来,由于整体的很多原因,我每拍完一部都不想再拍了,可是后来又拍,我觉得有一点被上天指派的感觉,上天让你做的事情,搞不好是个礼物。
后来我都觉得是个礼物,因为做出来作品之后非常开心,而且你也知道,让我开心的通常不是卖座,我意识到自己有非常大的创作,有很多人支持你,那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凤凰娱乐威尼斯独家专访蔡明亮
我的电影都很华丽,因为我太讲究了
凤凰娱乐:您的作品我一路看过来,有这样一个感觉,早期的一些作品好像有一点脏脏的感觉,但是最近的这几部都是非常精致非常华丽的,昨天虽然你是拍一个废墟和水,但是非常的美。在美学方面有改变吗?
蔡明亮: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我的电影,因为不见得是在银幕上看的,其实我的电影每一个都很华丽,真的,我不骗你的,看你怎么看,因为我太讲究了,我的摄影,我的光,比如像《天边一朵云》,或者是《洞》,当然有一些是旧的。
那天有一个孙松荣教授,他在北京出了一本书,然后跟我在台北做一个对谈,他就剪接了我以前的影像给学生看,我就忽然间吓一跳说这么漂亮,这么幽默,这么好玩,但是我回头想说《郊游》简单的一部,《郊游》什么音乐都没有,都是现场的声音,甚至没有一个漂亮的房子,除了一个样品房,都是废墟,最后我自己可安慰的就是,还好有个李康生,有非常饱满成熟的表演,我觉得他就是我很大的成就。我的演员不一定只有李康生,杨贵媚一个镜头,就哇,我说你一个镜头,我说是我看到你所有作品里最美的一次。
凤凰娱乐:为什么她只有一场戏?
蔡明亮:他们就很了不起,不计较,我觉得需要一场,她就来了,一般她不来的,她不愿意,但是她义不容辞,就来了。本来整个角色是陆弈静在演的,陆弈静也没有意见,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在想的是整个作品的完整性,或者创意性的表达。
不为观众拍片不是为了丢掉他们,而是为了改变他们
凤凰娱乐:你希望观众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多一些对边缘人物的关怀吗?
蔡明亮:电影与所有行业都一样,要有它的正面性,但问题是整个人类的价值观在改变。你发明一种药可以治病,但你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它可以救人,而是它可以赚钱。现在的人改变了世界什么?是快速的开发吗?不为观众拍片不是为了丢掉他们,而是为了改变他们。我的电影如果是艺术品,它就在等待你的使用,然后改变你。
我对亚洲电影状态比较清楚,大部分电影都变成了商品,整个社会对电影的关心在于票房,这个问题从以前到现在没有改变过,要改变现状,就要有作品,要有不一样的作品。这些问题都好严肃,难道我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导演吗?我的电影是最好的测试,如果能在大陆或者马来西亚放映,就说明那里的环境变了,很多地方没有真正的创作,因为有那多的限制,不是政治的限制,而是钱的限制。
我们的电影资金很少,因为很少,反而自由。最自由的是《郊游》里的这些人,这些野狗。
凤凰娱乐:这个电影里面有没有融入佛教的概念?
蔡明亮:我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刚好一直读《金刚经》,《金刚经》最有趣的就是辩证的概念。我们的佛祖,他们那批人,佛的弟子,或者佛讲话的方式是用辩证法的,是菩提又不是菩提,又是菩提。所以它是反反复复的,没头没尾的,但你要在里面去找到他真正要说的那个争议,因为如果他都告诉你,你不去找,你就不会去思考。
所以我这个电影其实是没头没尾。我今天看得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它好像很轻,其他非常重,就是轻轻的,什么都没说,家庭生活非常重。那它有点像回马枪,真的发生过还是一个记忆,都可以,就结束了,在那边还没发生事情就结束了,我特别喜欢这个。
凤凰娱乐:为什么电影里有条狗叫“李登辉”?
蔡明亮:那个是巧合,没有不尊重,李登辉是跟我一起看过《爱情万岁》的“总统”,但是刚好那条狗,它的主人就叫它“李登辉”。台湾是OK的,完全不担心会被人家骂我不尊重,台湾太民主了,里面还有一条狗叫“王力宏”,也不是我乱取的。

电影《郊游》海报
导演自述(文/蔡明亮)
十年前我在台北街头看到一名男子在路边举牌卖旅游行程,那一刹那很震惊。在红灯前的几十秒的问号……他到底要站多久?多少酬劳?他去哪里上厕所?会遇到亲戚朋友吗?会羞耻吗?他在想什么?
他像一根电线杆、一面墙、一棵树……没有人理他,他也不理人。
不久,这个行业如雨后春笋,房地产的举牌人布满街头,失业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有的是时间,但他们的时间不值钱,都去举牌卖房子了。
我当时兴起一个念头,要让小康来演这个角色。
三年前,接到一个关于中年失业、家暴的剧本,又想起那位站在街头的举牌人。
那些举牌人,每50分钟可休息10分钟,小便、喝水。一天要站八小时,只能举牌什么也不能做。我观察到他们有些喃喃自语,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就请小康唱《满江红》。这是中国宋朝抗金名将岳飞作的诗词,抒发对国家的满腔热血与壮志未酬的愤慨。四十几岁以上的台湾人,几乎都读过这首词,我曾听小康唱过。
西化的亚洲城市,让我感觉似乎处于无地基的浮动状态,有一种长时间焦躁不安的氛围。我们好像永远生活在工地里,房屋、马路、捷运不停翻修拆建之中,有更多开发,也有更多遗弃。
一直以来我的影片,从不避开这些景象,那些正在搭建的水泥工地,或是惨败的楼房废墟,只不过是再再展示出现代文明开发的疯狂特质和荒谬的丑陋代价。
《郊游》里描述一个单亲家庭,没有妈妈的角色,其实也没有“家”,“家”变成了废墟,父子女在一个又一个的废墟里移动。影片里我所拍摄的废墟,它们仿佛在那里苦苦地等着我,那些场景我视它如同一个个活生生的角色。我找到它们,同时聆听它们诉说自己的故事。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在一面墙遇到一幅巨大的风景画,很震撼。这幅画是这个寂寞城市的一个表情吗?还是一面镜子?映照着人世的虚幻或实相?画的人不知是谁,我决定要拍它。我要求剧组保护它,没有人有办法,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废墟,我只有祈祷。
直到后制的时候,才查询到这位艺术家叫高俊宏,近年来开始在废墟做绘画创作。有趣的是,他跟我说他没有所谓展出的形式,只是希望这个作品被人遇到。所以,我们相遇了。
更有意思的是,俊宏其实画的是一张老照片,1871年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生拍下了台湾南部一处山水风景,是100多年前的原始地景。照片左角原本有两个平埔族小孩,俊宏没有画上去。
很巧,在我的影片里,也有两个小孩在废墟里游荡。
剧本里原来只有一个女人的角色,她介入小康的单亲家庭夺取他的小孩。原本属意陆弈静来演,后来我身体很不好,总觉得自己随时会死掉,很可能《郊游》是我最后的一部电影,恐怕没有机会再跟杨贵媚、陈湘琪合作,我突发奇想,为什么不找三个女人来演同一个角色?后来拍出来,她们是不是在演同一个角色,好像也不重要了。如果这是我的谢幕,我很高兴,我喜欢的演员都在我的身边。他们一直都在我的身边,不管角色大小,我很感激。
我也感谢我的干儿子和干女儿,我看着他们出生和长大。他们是小康的侄子,都不怎么喜欢演戏,哥哥李奕?三岁就演《不散》,五岁演《是梦》,每次都是半夜把他摇醒上戏,现在他是国中生了,勉强再来演一次。七岁的李奕婕,开始根本不肯演。结果一上戏,精彩极了。
要不是小康,我也不会拍这部电影吧。
对电影我已倦怠,近代电影所谓的娱乐属性、市场机制、大众口味,令我反感。我不觉得我要一直拍电影,更直接地说,我不觉得我还要拍那种在院线等着观众来买票的电影。我总是在问,电影是什么?为什么要拍电影?我在为谁服务?大众是谁?是看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那些人吗?老实说,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在2011年,我跟小康合作一个舞台剧,排戏时他一个慢走的表演让我震动,我脱口而出:“康,原来我们合作了20年,就在等待这一刻。”
剧场朝生暮死,演完就没了,我又升起了拍片的冲动,于是开始了小康《慢走长征》的短片拍摄计划,我在想,我还要再拍小康那张脸,而且放大。
漫长的20年,这张脸在摄影机的注视之下变成了什么?或者显现了什么意义?《郊游》的拍摄计划,其实只是一个手段,从剧本到拍摄到剪接,历经三年,我最大的功课,就是去故事,去情节,去叙事,去结构,甚至去角色。就只是这张脸,在某一段行为之下的一张脸的完全呈现,其中一个镜头,我给了小康一颗高丽菜叫他吃掉,然后开机,我不记得给了他什么指示,或许我什么都没说,我看着他,从容的、安静的、怜惜的、感伤的、怨悔的、寂寞的、满足的、酸楚的、爆裂的……啃、咬、塞、咀嚼、生吞活剥、爱恨交错……我看着他,用他人生的20年吃掉那颗高丽菜,他哭,我也哭。
从1991到2012,最终我还是要说,他的脸,就是我的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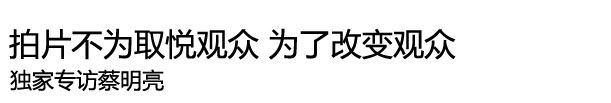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