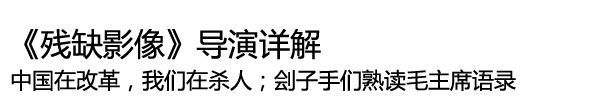
中国看客尤其喜欢从奥斯卡中找亲属关系,去年找到了台湾人李安,今年却没等到《一代宗师》,挺遗憾的。但更遗憾的,其实是这两部被本届奥斯卡错过的提名影片,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的《杀戮演绎》和最佳外语片提名的《残缺影像》。这两部电影唯一能称之为有趣的地方,是他们在内容上互文,在创作形式上也想和其他同属性电影做出区别。华人在其中都不是主角,但却是不可取代的配角,是作为证据的血渍。这里没有任何娱乐意义,面对小李子十年影帝梦破碎的委屈,他们在普罗大众面前甘拜下风。我们不想用煽动性的话诱惑大家对这两部电影的关注,你只能自己去看,也许因为评论网站的高分,也许你推崇“革命”的概念,也许你身在其中。
文/波米

《残缺影像》导演潘礼德其实早被国内很多东南亚电影爱好者所熟知(Bophana center供图)
记者手记:
在奥斯卡提名揭晓后,我们没在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名单里看到《一代宗师》的身影,除了几部大热门,意外上榜的是一部柬埔寨电影:《残缺影像》。如果你简单查询过它的信息会发现,这是一部讲述70年代柬埔寨共产党大屠杀的电影,在那场与中国关系微妙的大屠杀中,柬埔寨整整有1/8-1/4的人口被屠杀,而《残缺影像》则用看似轻易的黏土动画承载了这样一个如此沉重的主题。
《残缺影像》的导演潘礼德如今的头衔有两个:一是柬埔寨首位奥斯卡提名者;二是那场屠杀的幸存者。显然,他的第二个头衔戴在头上的时间要更久:1975年,11岁的他和很多柬埔寨人一样被投进了劳改营,屠杀的4年间他失去了许多亲人,随后他逃往法国,在巴黎认识并学习了电影。在此之后,他返回柬埔寨,用电影生涯90%的电影作品都对准了同一个题材:“红色高棉屠杀。”
在奥斯卡颁奖之前,我们电话采访了正准备从金边启程前往洛杉矶的潘礼德。因为他作品中极强的政治含义,我们下面的采访也并没有紧扣电影本身。而对于“红色高棉屠杀”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我们则采访了曾发表《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一文的著名历史学家程映虹教授。我们深知,红色高棉惨剧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正如潘礼德在采访中所说:“早晚有一天,你得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那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记忆,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
(“柬埔寨共产党”、“赤柬”在以下访谈中被通译为“红色高棉”)
潘礼德揭《残缺影像》拍摄理念:人都会像黏土,化为尘埃随风而逝
凤凰电影:在你2005年那部《被烧毁的剧院的演员们》(后简称《演员》)中,有一段女演员对着一个房屋模型回忆起红色高棉暴行的场景给我印象深刻,《残缺影像》的模型概念可以被看做是那一段的延伸吗?
潘礼德:从某种角度上讲是这样的,都是关于柬埔寨回忆的讲述。但是《残缺影像》更倾向于一部纪录片。《演员》更多关乎在战后幸存的艺术家们多年后的生活描绘和回忆,它更像是一幅战争后果的展示图,而《残缺影像》则更重在讲述大屠杀过程中人们那些真实的经历。

《残缺影像》以看似轻易的黏土动画承载了一个沉重的屠杀主题(Bophana center供图)
凤凰电影:可能所有采访你的人都会问,《残缺影像》为什么会选择以黏土动画的形式呈现?
潘礼德:首先,《残缺影像》并不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动画片。我们只是用了黏土小人的形象。我本来想做一部非常传统的纪录片,但是我突然得知我一个助手可以捏黏土小人,我让他为我捏了一些,然后我发现这其实是个挺聪明的创意——这些黏土小人其实带有很强的表现力。而且这些黏土的构成就是土和水,在拍摄结束后它们又可以重回自然,十分环保。当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些小人不仅仅是黏土形象,它们更代表了人类的精神本质:每个人最终都会像黏土一样化为尘埃随风而逝。在柬埔寨,我们对菩萨祈祷,对石头祈祷,只因柬埔寨人相信万物有灵。我们懂得,当一个人死去之时,灵魂不会随之而亡。所以这些黏土捏成的小人,也正代表了那些在屠杀中的死难者之灵。除此之外,这对于我也不再是一次简单的纪录式拍摄,它为我带来了全新的体验。毕竟,我也是屠杀的幸存者之一。当一个屠杀幸存者作为导演去不断表现屠杀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一直是五味杂陈的。而这一次“黏土”让我找到了一种更加舒缓的表达之道,对我自己亦是一种宽慰。
凤凰电影:整部《残缺影像》的投资有多少?制作周期多长?我知道《S21》那部电影的融资过程非常艰难,这次有没有遇到类似困难?
潘礼德:关于投资,我其实并不知道确切的数目,因为我的法国赞助商也投资了一部分。这部电影耗资有些高,主要原因是拍摄时间比较久。如果三个月就可以杀青,估计只会花2万美元,但是现在拍了两年,理应就要花更多的钱。
对我们来说,做这件事最难的其实是收集人们的记忆。通常我们在制作一部纪录片时,我自己都不清楚成片的最终“样貌”,我们都是先去采集素材,然后再一点点 剪辑,逐渐才能看到电影的轮廓。有时候这一过程要在三年以上,比如《S21》。而《残缺影像》则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了。你也知道,生 活如此,万事皆不易。

潘礼德:黏土捏成的小人,也正代表了那些在屠杀中的死难者之灵。(Bophana center供图)
潘礼德谈红色高棉:每一个人都对这件事负有责任
凤凰电影:在中国也有很多关于红色高绵的讨论,你作为一个屠杀的亲历者,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潘礼德:我们都生活在亚洲,都需要了解和清楚彼此的历史。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红色高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当时也有很多中国的学者也来到了柬埔寨,给红色高棉提这样那样的建议,可红色高棉也同样在屠杀华人。我一直不太明白的一点就是:当时红色高棉也在杀害华人。在1975到1979年那段屠杀的时间里,中共的领导人已经开始试图走出文革,一点一点的改革开放了,但红色高棉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真的不太理解,虽然这可能就是政治吧。这或许也是党史的写照:苏联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等等,彼此的理念一旦不同,就要死人。其实,这些事都应该有人讲出来的,我们都需要接受曾经发生的错误,并试着矫正这种错误,不然这就会成为历史的遗恨,也会成为你我每个人的损失。
你要知道,红色高棉的屠杀是一次大规模杀戮,是种族的灭绝,是反人类的犯罪。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每个人,每一个人都对这件事负有责任。虽然这件事发生在柬埔寨,但它将来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不是说苏联或中国有什么作用的问题,而是屠杀发生根源的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在和平年代死去?正如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一样。这些情况都是不多见的,即使在国际共运史上也不多见。所以让我们坐下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错了,这非常有必要。
凤凰电影:你提到中国的文革。其实在我参观S21时就对一幕颇为震惊:当时我看到有许多柬埔寨的小学生也被组织去集体参观S21,很多人还拿笔抄写牌子上的资料介绍,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从你的角度,你是否认为如今柬埔寨对这场屠杀的反思态度已经足够端正?
潘礼德:首先,S21纪念馆的建立是十分必要的。至于足够端正……如果你的意思是问我在这点上柬埔寨是不是比中国做的更好?我想说是的,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你必须得对过去做一个解释,因为人类共同的记忆是无法被磨灭的。人们希望了解真相,总有一天,下一代人会指着我们问:“在我们祖父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是不是杀了人?”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他?早晚有一天,你得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那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祖父们到底是杀了别人抑或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记忆,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
凤凰电影:在《杜赫:炼狱魔王》那部纪录片里,侩子手也说毛泽东语录对他们影响颇深,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就你了解的情况来看,是当时每一个红色高棉的党员都会学习毛泽东思想吗?
潘礼德:那段时间他们读了很多毛泽东语录,也见证了很多在中国发生的事。其实毛泽东自己也知道在文革中有很多人因为饥饿而死去了。红色高棉不是没有目睹中国的惨状,他们只是相信自己可以比中国改造的更彻底,可以让国家发展得更快,但事实证明他们没有成功。
凤凰电影:就你了解,毛的哪一句话在当时的柬埔寨最为人熟知?
潘礼德:很多话都很熟悉。例如,毛曾经有过关于阶级的描述,他认为中国分为三到四个阶级;柬埔寨就照猫画虎的认为我们只应该分两个阶级:工人和农民。但实际上这样分是毫无道理的。不是每个人都能被粗暴的划分到同一阶级里,然后头发剪得短短的,每天只能穿素衣出门……可红色高棉当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效仿斯大林体系,然后发明了一种混合体制。
凤凰电影:那你有没有想过拍一部讲述红色高棉与国际共运联系起来的电影,对准上层建筑甚至外交关系?
潘礼德:我们更多的责任是去呈现在柬埔寨发生的悲剧,而且我们不能说屠杀就都是外国某种政策的结果,我们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只是国际共运确实对柬埔寨产生过很大影响而已。怎么说呢,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只能试图呈现一些历史的注脚,以供人们在电影中回忆那段经历。只有了解历史,才能进步。

很多潘礼德纪录片中同样出现了《杀戮演绎》中“侩子手重演侩子手”场景。
潘礼德谈伤痕作品与屠杀电影:我很喜欢杨继绳著作 《辛德勒名单》没法看
凤凰电影:在中国经历文革之后,涌现了一大批反思文革的艺术作品,它们被统称为“伤痕文学”。如果有人把你的作品称为“伤痕电影”,你是否会认为这带有某种轻视?
潘礼德:每 个人都可以把涉及同一类题材的作品盖以一个他们觉得合适的头衔,这也是大家的权利。只是……就拿中国来说吧,你也不能说文革之后的作品就都能用“伤痕文 学”一言蔽之。你应该知道杨继绳吧?对啊,我很喜欢杨的作品,他的著作同样纪录了文革,但就不能属于“伤痕文学”的范畴,我们也一样的。
凤凰电影:回到你拍摄的《杜赫》那部纪录片,杜赫在片中将自己辩解为一个命令的执行者。我们都知道,像汉娜-阿伦特这样的学者也曾把屠杀中的施暴者根据动机一分为二——大多数人只是“平庸的恶”。我知道你对此十分不以为然。我在想,这或许是因为你接触的很多罪犯都拿这套理论来为罪行开脱……
潘礼德:是所有的犯人!所有犯人在面对法庭质问时,都会有类似辩解。他们会说自己只是命令的执行者,可这就完事了?有时候我们需要对命令说“不”啊,尤其是当这项命令是在催促你去杀人的时候,那么违抗命令或许就是你的责任。但杜赫做了什么?他服从了命令。很多人在接受审判时在装无知,但杜赫其实很聪明,他能掌握好几门语言,有非常高的智商和情商,他有能力去判断是非:判断哪些命令该执行,哪些不该,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也是施令者之一。
凤凰电影:你曾在以前的访谈中对比过波兰斯基的《钢琴家》与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你当时认为前者要比后者有才华的多,可以具体谈一谈吗?你是否认为《钢琴家》更出色是因为波兰斯基本人也是屠杀亲历者,正如你与你的作品一样?
潘礼德:有这种可能吧。当然,我不否认斯皮尔伯格是个好导演,只是对于我来说,《辛德勒名单》没法看,我根本无法接受导演那种呈现方式,比如摄像机对准受难者走进集体浴室那场戏,太戏剧化了……但是当我观看《钢琴家》的时候,它给我一种强烈的压迫感:让你不用眼睁睁地看着灾难发生的压迫感。这其实事关动机,审视一场大屠杀一定要从动机着手,即从根源去讨论悲剧发生的原因。
凤凰电影:今年有一部拿到奥斯卡提名的电影《杀戮演绎》也是反映屠杀的,你看过那部电影吗?它对屠杀的视角你是否认同?
潘礼德:看过,我和导演本人很熟悉。《杀戮演绎》其实探讨的远远不止杀戮行为本身了,它所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会成为杀戮者?在杀戮者身份的背后他们还是什么样的?以此去追问那个终极命题:“屠杀为什么会发生?”事实上,很多纪录片导演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尝试解答这个问题:约书亚聚焦的是印尼屠杀,而更早以前的朗斯曼则关注纳粹屠犹(《浩劫》,编者注),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都试图在采集与拼凑素材的过程中为屠杀找到一条出路,可我们都没有办到,都没有。我自己至今都无法拍摄出一部完完全全解释屠杀的电影,我能做的只是尝试让观众回忆起一些片段,迫使他们感受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如此而已。
凤凰电影:如果你最终获得奥斯卡,你认为它的意义更多在于令世界认识到红色高棉这场屠杀的存在,还是会更多促进本国人对红色高棉的最终审判?
潘礼德:关于奥斯卡,我想说今天我站在这里就已经赢了。我有能力拍出这部电影,表达我的观点,把我的情感告诉全世界,这已然是胜利。红色高棉对我造成了伤害,但他们无法摧毁我,他们杀掉了我的亲人,杀不掉我们的思考和想象力。我将不是一个去奥斯卡,全柬埔寨人民都在我身后,这是我们第一次有这样的殊荣,整个国家都在以此为荣。(记者:关于审判呢?)我希望这部影片可以陪伴着我们,直至最终审判结束的那一刻。对红色高棉的整个审判进程比较缓慢,我确实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对加快审判的进程有所帮助。
(采访、撰文:波米)特别鸣谢:橙小天女士及彭衫女士

《残缺影像》电影海报
专访历史学家程映虹:理想化的审判在当代社会中是很难实现的
记者:我曾看到过您在写杜赫时他晚年信奉基督教之后的忏悔,但在潘礼德的《杜赫》纪录片里,他面对曾经下属的指 控还是一副逃避和辩解的态度。潘礼德说在他的调查中,很多受审的红色高棉中高层都在用“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理论为自己开脱——事实上他们都很聪 明;而《杀戮演绎》里印尼的杀人狂在大部分时间里甚至毫无悔意,您有没有关注过这些“战犯”的犯罪心理?
程映虹:我是这样想的,碰到这样一个极端情况的时候,人开始也许会狐疑、会思考,但杜赫这些人可不是简单的杀一两个人,他是杀人如麻。这时心理是会产生变化的,谈这 一点时可以把历史背景虚化掉,他实际上只是一个犯罪心理学的问题:“麻木”。有的人“麻木”有的人“轻松”,到最后就“杀人”就变成“走程序”了,我去看 过德国的集中营,有焚尸炉那些东西,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会发现其实它更像一条流水线,杀人的人其实就像是在做普通工作一样,每天招进来一批,杀掉一批,然 后送出一批焚烧,这些人在当时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想法,而且人的心理到了这个时候也会自然而然有一种反应机制产生,你看有少数杀人者后来疯了,而 大多数情况下,人为了防止自己疯掉会出现一种心理上的防卫机制,才让自己逐渐麻木。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理承受极限,到了那个极限以后,当防卫机制起作用,人 就不会在去思考或内疚等等这些反应了。
那么在杀人之后呢,这时又需要谈历史背景的问题。像杜赫这种人,他认为自己在大的方向上是没 有错的,起码原则上没有错,只是具体到屠戮生命来说他开始感到有愧疚感,但是屠戮生命这个动机,他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这就像你去问当时参加过土改文革的那 些中共老干部,他们可能也会是这样想的。
记者:在您的研究看来,红色高棉、中共与苏共之间存在“改造社会激烈程度”的递进关系,红色高棉认为我们不够彻底,就像我们认为苏共是“修正主义”一样,中苏关系破裂可以用“利益矛盾”来解答,但红色高棉这种思想又是如何形成的?
程映虹:这个要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在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希望消灭“三大差别”:阶级、城乡和脑体之间的差别。这三大差别我们听上去抽象,但要具体落实到政策上,无非就是“市场、货币和官僚制度”,那与此相联的制度、规范和惯例都是由这三大差别而来。人类社会的文明史,首先就是要讲分工:人类社会生产力提高的越来越快,分工也就越来越细。但是革命是要把这些分工全部消灭的,只是具体到政策上要如何消灭呢?就是把教育废除、货币废除、城市废除……只要他信奉这个理论他就会这么做。那么红色高棉在实践上就会让社会形成一个倒退:把城市撤空了等等。所以,红色高棉这个思想首先是从共产主义思想创始人的理念而来的。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的理论不是这样简单化的,只是后来人在执行的时候是这样理解的。
而另一个原因可能更重要,就是所有共产革命的领导人在夺权之初都没有管理国家的经验和能力。共产党初期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知识分子,一种草根人士。这里的知识分子还不是技术型人才,是法国大革命那种游离于社会边缘的、空有政治抱负和政治野心的、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还有就是一帮草根人士。这些人的出身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夺取政权后无法正常管理社会,所以自然整个社会会朝着原始社会的方向倒退。这时,他们会想出什么办法呢?革命,他们会认为是革命还不够彻底,其实他们这是想回避自己的短板,这其实正是他们知识上有所欠缺的反映。
所以说是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共产党掌权有一个“社会改造激烈程度”的对比,说穿了这不是改造而是倒退,就是原始化倒退,像我们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就属于倒退,是社会管理运作的倒退。这个倒退的概念有人试图用“乌托邦”来解释,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就不是理论上的问题,实际上“倒退”就是因为这些人不懂、无能,仅此而已,所以他们才要想找出一个所谓“彻底的”实则“简单粗暴的”办法。
这时,才能开始回答你的问题:“改造社会激烈程度”的递进关系,我们不妨来对比中苏之间的关系。其实中共应该算是世界上所有共产党革命当中最有管理经验的了,因为中共长期有“根据地”经验,工商业经验在那时都有过一些,他连走私鸦片也搞过的,在内战时也夺取过城市,所以中共还是相对有管理经验的。所以我们看到它在建国后的50年代上半期还不是太差。
但是一旦过了那个过渡期以后,它的本质就暴露出来了:空想共产主义。这具体体现在了毛和刘少奇的分歧当中。刘少奇这派已经可以逐渐管理社会,但毛泽东是有急切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只是真要着手去管理社会时他又不行。后来文革开始其实意味着毛没有完成斯大林式的过渡,斯大林是完成这方面过渡的。当然在斯大林之前,布尔什维克党更没有经验,它们没打过仗,没过“白区红区”的概念,一下子就把他放到了国家管理层面,那么列宁的方法就是“机关枪管理银行”,一下子过渡到共产主义。他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把粮食和资源全都抓在手里。但是从我的角度来分析,他也只能依靠这个措施——不断进行战争才能继续维持“空想社会主义”的措施,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要完全打垮,是因为他们也不懂那种管理社会的方式,这个才是最深刻的原因。但是到了斯大林,他基本上算是建立了一个官僚制度,所以斯大林本质上是不同于毛,也不同于红色高棉、古巴的。
记者:那红色高棉与中共之间的递进关系呢?
程映虹:这个很清楚,我在1999年写的《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里就提到过,这是当时我在阅读西方材料时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红色高棉与中国“文革”的关系紧密。红色高棉其实是以文革为鉴,这个借鉴不是说文革搞失败了所以我们就不要搞,而是文革搞失败是因为它革命的还不彻底。红色高棉本以为1978年中国要再来一次文革的,结果当时中国准备改革开放了,所以它自然形成了这种认识。这里的问题是什么?是红色高棉认为现代国家制度所带来了三大差别,“以城市为中心”这整套制度使他感到恐惧,他驾驭不了、改造不了,他会想:毛泽东花那么多年都没把这套制度改造完成,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干脆就不要改造,全部摧毁它!所以对红色高棉来说,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对他来说只是如何在最短时间把它废掉的问题。
记者:今年是对“红色高棉”反人类罪审判的最后一年,但由于这个审判周期太长,很多红色高棉的高层领导人早就已经去世了。您如何看待这类审判?
程映虹:我觉得它其实有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冷战的遗产和盲目革命的伤疤还在那里隐隐作痛。对于中国来说,当然还有它更特殊的意义,因为中国还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没能清算,所以对中国来说这类审判尤其重要。
(记者:但有些国人认为这类审判是西方操控的,有人则认为它周期太慢……)任何“大审判”都是“政治审判”,都不可能仅仅是司法审判,政治因素必然要起作用,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像红色高棉这样的审判也绝不仅仅只是柬埔寨的内政问题,哪怕主要是在它国内审判,也要去考虑国际影响,比如它要考虑中国的反应,在审判过程中不能更多把中国人牵扯进来等等,它不可能只是像审判一个刑事案件一样纯粹是“司法因素”起作用,其实包括像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它很大程度上不也是各种力量角逐和平衡后的结果吗?但审判毕竟还是审判,左派好像总是认为只要是审判就只能从司法层面进行,否则就没有意义,那么慢啊又那么多政治脚力干脆取消审判就完了,这实际上是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了,理想化的审判在当代社会中是很难实现的。
(记者:其实我从个人感情能够理解持这种说法的人,这出于人们一种很朴素的心理,我自己有时也想不通:如果你只杀了一个人,你可以马上被抓被判刑,在死刑国家甚至还要“血债血偿”,但当你杀了10万人、100万人,就像波尔布特这样的人,反倒很长时间不会被追究什么责任,直到波尔布特寿终正寝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去追究他。一种“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感觉。)是,当你的杀人行为上升到政治层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采访、撰文:波米)
策划:凤凰电影小组
撰文:波米
责编:法兰西胶片
监制:田野 李厦
出品:凤凰网娱乐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