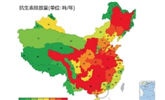来过 爱过 被听到过
2016年04月05日 00:43
来源:北京青年报
电影是个梦,生命是一场离散。来过,爱过,被听到过。这是刚刚过去的冬天,老影人们教给我的事。
“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
又是清明。这一个春日谁是我会怀想的逝者?我又在哪里遇到他们?
定福庄东街1号24楼——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它的二层有个电影传奇馆。
对,就是那个小崔爱现好演的“电影传奇”。2004年4月3日至2009年9月27日之间,它是央视一套《东方时空·周六特别奉献》一个气质有点怪怪的栏目。其实它的背后是一个浩繁周详、富于创意和超级耐力的口述影像采集工程,开始得比节目播出早得多——2002年夏天,电影《小兵张嘎》中“嘎子”一角的原型赵波,成为第一个被访者;持续更是直到2015年。最终,它的采集成果是超过1900人次,190000分钟。
13年过去,“口述历史”从生字变成了一个热词。小崔和他的团队,也换掉了央视的身份,成为八通线上那个青翠校园里一个特别的存在,有点像一队怀抱珍宝、神秘孤高、不屑于被理解的孤军。
老影人口述的首次大规模对外开放,来得有点儿声势清淡。2015年11月17日至2016年1月20日的每个周二、周三,还赶上刚刚过去这个寒冬几乎所有的雾霾天。
每天,原则上可以有16位通过网上或电话预约的来访者,进入这个电影传奇馆。每人挑选一位老影人,电脑前听一个小时他们面对镜头或安详或悲喜的讲述。都是从未对外开放、也未经剪辑过的影像。第一批被开放的,都是逝者,都已往生。
电影传奇馆很大,暖气很薄。各种年头久远的放映机、老照片、旧海报、有故事的物件,静静安放。有人参观的日子,背景音乐就会开。是周璇气如游丝的《四季歌》,好像还有老唱机针头划过老唱片的嘶嘶声,无尽往复。在耳机中老影人们每一间歇、沉吟、甚至泪下的静音处,悠悠地浮起在身边清凉的空气里。有几回,碰巧整个馆里只有我一个人,恍惚间会觉得周围有很多灵魂。
开放持续了64天。尽量去坐了每个可能的周二周三、上午下午,也只听了14位老影人,听到14个小时。手写了上百页笔记。望着眼前屏幕上那么温暖生动的脸,听他们说着过往、此生的朋友、历经的苦厄,觉得能和他们在一起是那么好,互相陪伴好像永远不会孤单。然而,回神惊觉的一刻总是会来,记起他们已经是天上的星辰……那感觉让这个冬天无法寻常。
电影是个梦,生命是一场离散。来过,爱过,被听到过。这是刚刚过去的冬天,老影人们教给我的事。
每一个口述背后 都有一个很生动的生命
挑选随机到盲目。
有的看他聊得长,比如演员吕玉堃83岁受访,一次访了6个小时;后来才知道还有更长的,导演王为一91岁受访,一春一秋两次,总共聊出16个小时;
有的感叹活得久,导演汤晓丹102岁辞世,而且《渡江侦察记》耳熟得亲切;
蒋天流,碰巧小西天看过《太太万岁》。文青爱争说它的编剧张爱玲、导演桑弧以及他们间若有若无的情事,几乎没人关心它女主角饰演者的名姓;
然后演员张鸿眉,资料上她年轻时的照片我觉得好看,听了才知她是费穆《小城之春》里的妹妹戴秀;
所有人理想中都想要的“爷爷”李丁,我爱他的《天堂回信》;
把老版《林海雪原》的杨子荣演成了一个武侠,王润身那张京剧脸很好认;
从部队走上银幕的徐连凯和30岁起就演老太太的陈立中,共同让有关《花好月圆》的记忆完整;
让人猜想比年轻时还美的银发林彬和自诩演了一辈子反派的夏天,原来他们都演过《秋翁遇仙记》,那个小时候看过、印象模模糊糊的古装神话片,让我一辈子对开满牡丹的花园没有抵抗力;
吴天忍,原来《苦恼人的笑》是他导的;胡炳榴,当年气质抒情的《乡情》出自他手;
最惊喜的是演员李唐,《甜蜜的事业》里那个“女儿迷”老莫没有人能忘得了。1979年谢添导演的这部喜剧片,从人物到歌到男追女跑的慢动作,还有李秀明的眼睛和手中的纱巾,都无不明媚。
“电影中天气好,人物表情健康美好。无论年轻男女,无论大爷大妈,都热情明媚助人为乐,那是一种全民的青春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虽然今天看看有许多概念化的地方,但是那种青春中国的‘晴朗性’却感人至今。今天的银幕上,我们有过十分钟的好天气吗?”影评人毛尖老师这段话,《甜蜜的事业》生生就是它的注解。
“这些积累源自于13年前到现在。”口述中心“老电影人”和“知青口述史”两个项目的主持人赵一工,用一种让人几乎无法理解的意兴阑珊抵触媒体采访,以至于只能到去年12月5日中心主办的“口述研习营”课堂上,去听到只言片语他对自己工作的感受——
“刚才他们介绍我‘个人采集三四千个小时,一千多人’什么的,可能是按我们工作量标准的一种说法。其实这个数字确实不是这么冰冷的,有特别特别复杂的内涵。比如这十几年中,我还参加过几十个葬礼,拟定过超过100份的唁电,我还参加过很多的生日会。每一个口述背后都有一个很生动的生命。”
他们在口述回忆里师友全聚
更多已经无法亲自讲述的人的生命,是被这些坐在镜头前的老人的回忆标注出来的。比如赵丹和谢添。
导演王为一老人在受访10年后仙逝,享年101岁。2003年1月第一次采访他,上来就聊了12个小时。而那年他已经91岁了。最终他的受访总时长是16个小时。“王为一导演的高寿以及超强的记忆力和思考能力,使他的口述成为中国电影史的‘活化石’。”大家必须在他的简介里加上这句话。
王为一老人的口述,我听到的只有十六分之一。印象最深的是他不断提到的赵丹:“他对舞台的爱,一般人想象不到。”
才知道赵丹生在杨州,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南通。他父亲在南通开了一家影戏院。电影、舞台剧、京剧之类,只要有观众看的、能上台的,都演。而他的同学顾而已的父亲是中学校长。两个条件加在一起,就积聚了一帮“爱搞戏”的少年——赵丹、顾而已、钱千里、朱今明……平时一起读书,排了戏就到父亲的影剧院演。
后来上海剧联有个摩登剧团到南通去演出。赵丹这帮人就天天坐在台底下每场看,看到台词都背得出来,“这才是真正的话剧”。不在台下看的时候,就在后台混。剧团走的时候把剧本都给他们留下了。他们就自己演这些戏,叫个“小小剧社”。那时赵丹才十六七岁。
因为演这些进步戏被当局盯上,少年们一齐逃到上海。赵丹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国画;顾而已到大学念书;朱今明到工厂学机械。赵丹、徐韬、王为一同为美专剧团骨干。经当年去南通的赵明已介绍参加剧联,从此步上“进步”道路。知道剧联是共产党领导的,还以为参加剧联就已经加入组织了。到解放才知道,“哦,我们还不是党员。”
1939年,已经是电影明星的赵丹和好友徐韬、王为一、朱今明等10人结队赴新疆。至今网上搜到的说法都是他们被盛世才“和平、建设、民主、民族平等、亲苏、团结”六大政策迷惑,赴疆开拓新剧。
64年后,王为一老人在91岁高龄的回忆,才揭示出那其实是一次青年人电影梦想的热情历险:“真可以写部电影。不是组织派遣的,是我们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想通过新疆去苏联,到斯坦尼艺术学院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回国搞一套电影体系。我们是组了一个班子想去学的——我跟赵丹是搞导演和表演的;徐韬是搞管理的;朱今明是搞舞台的,到那边全套都要学,包括舞台装置怎么搞;还拉了一个搞音乐的人去。”结果路过新疆时被军阀盛世才逮捕,赵丹跟徐韬在迪化监狱被关了五年,王为一等关了四年八个月。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加入昆仑影业公司,任史东山的副导演参与《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拍摄,1948与徐韬合作导演《关不住的春光》,跟赵丹说“你从来没演过反派,试下怎么样?”很潇洒的一个反派,赵丹觉得有戏可演,意兴满满。
说起赵丹,另一位忍不住唏嘘的老影人是83岁的夏天,2003年他在访谈镜头前落下泪来:“讲到赵丹我还有点激动,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在重庆就在一个剧团,到上海跟他拍了好多戏。他真是一个好老师、好朋友、好演员,想象力丰富,浑身都有戏。他是个动作大师,在任何一个场景里面,他都有一个新的动作产生,而且这个动作是属于这个人物的,不是赵丹的。临场那个自然啊,不让你产生任何怀疑。我受他影响很大,他跟我说:‘你要用动作来表现你的情绪。’”
在夏天的眼里,赵丹近乎完美,唯一的缺点就是“带点南方口音”。“他说:‘我戏演得好,普通话差一点有什么。”赵丹留在他记忆里是骄傲的。
口述里除了电影史,还有社会生活史
李唐老人受访时75岁了,一口北京话,精神极了。
口述中心给准备的简介里属他的最短,不到200字。一小时他的口述听下来,才知道那是什么样程度的丰富和鲜活。
“以前年轻人很少看‘十七年’(时间概念,指1949年建国到1966年“文革”开始这一阶段)的电影,后来有的演了,他们发现‘很好!’那是花费了大功夫,真是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候的戏不管技巧怎么样,极端地像。”
有部在市面上只演过一天半的戏,《无穷的潜力》。谢添主演,东北一个钢厂的故事。全体下去到鞍钢当了一个月工人。
“在压延车间,工人们在一千多度的高温下工作,红光闪闪的钢条像火蛇穿梭在毛轧机与光轧机之间”。这是网上搜到的电影梗概。
“方辉演‘大李’,刚出炉、烧红了的铁条,必须一出炉就一夹送到那里边去。这个很危险。真正的工人有时候一夹没夹住,这么一抡,死了。又热又烤。那时候就得这样地学会。真干。”
李唐老人后来在电影学院考学生、任教,“那时候必须要跟工人结合在一块儿,你才有资格去演工人。不像现在,今天接一个剧本,明天就拍。剧本写的是什么,自己那个角色是什么,角色的职业有什么特点,可以都不知道。从生活中怎么来呀,你不是从生活中来,你能怎么能相信你那是真的呢?”
李唐老人看东西仔细:“那些个工人,三班倒。干活的时候穿着石棉的防护服,脏了吧叽的。下班,皮帽子、大皮衣,就跟那苏联人一样,好阔呀。刚去不熟,还以为参观的人来了,再一看才知道是换班来的。保健菜,一人发一盘炒木耳。这都是想象不到的。”
口述里不光有电影史,还有社会生活史。
李唐1928年生人,因抗战14岁失学,从北京回河北深县老家。后来在那儿参加进步的演剧队。18岁那年得了“砍头疮”,乡间无法医治。这时候听说,他的亲姐姐和姐夫抗战前留学法国读医学博士,抗战八年回不来在里昂一个医院里当大夫,胜利回来在天津,是知名的外科大夫和妇科大夫。
“人说你找她去吧,她一定能很快把你治好。但我是一个革命战士呀,天津是蒋管区,我这是解放区呀。这解放战争即将开始,我还有点头脑,跑那边等于投敌啊。”犹豫了很久,实在不行,他就写了一封信往离家一百里地的新集,跟组织请假。
“这信,你们大概都没听说过,没有邮政。每个小村都有一个学校,学校里的学生就是邮递员。我村学校派一个学生到邻村。邻村再往下传。那信也没有信封,就叠巴叠巴。就那么就能给送到。后来我问,还真收到了。”
口述道出时代的际遇和人的苦楚
《太太万岁》里大方美丽的蒋天流,2003年4月受访时82岁。她觉得自己的一生被浪费了。“唯一觉得《太太万岁》还比较满意,后来就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没有让你有发挥的机会。”
与《太太万岁》里石挥的合作也是难得美好的记忆。“石挥高高的,会说很多种方言。《太太万岁》之外,在他演戏都是很内在的,跟他配戏很舒服很舒服。从内心流出的那种幽默,跟他配戏能出来这个。”
后来她亲历了1957年石挥的死。“第一次大会已经批斗过了,第二次大家都默默地坐在大厅里等着开批斗会,说找不到石挥人了,一直找不到,后来说已经在黄埔江了。”
那是11月中旬的上海冬天,狂傲一生的“话剧皇帝”石挥在批斗会两天后,踏上他最后一部电影《雾海夜航》的道具船“民主三号”轮,那夜它从上海开往宁波。17个月后人们在海边找到了他完全无法辩认的尸骨。
活着的人还要熬过“转型”的煎熬。1951年,蒋天流和赵丹拍郑君里导演的《我们夫妇之间》,“很好的戏,非常可惜,演一个礼拜不让演了,写剧本的人出了问题。”
后来她跟郑君里导演拍《枯木逢春》,“那个时期没有好的文学剧本,都是很宣传式的。”她亲见郑君里导演的挣扎:“他也很苦的。他还是很认真,觉得要把自己转过来。因为知道没有以前那样的日子了,以后就是要做这一流的戏。”
那是上官云珠都非常努力地塑造工农兵的年月。汤晓丹导演的《南征北战》救了好几个人。张瑞芳演游击队长,冯喆演营长。以前更多演“才子佳人”的他们,在这个戏里完成了工农兵形象之后,重新被“新中国的电影观众”接受。在一场非常大的开会戏里,还有孙道临,一个镜头,还问了一个问题,最终成就了《渡江侦察记》,也得以在“新时代”银幕幸存。
汤晓丹导演2003年1月、2003年8月、2005年4月三度受访,其年分别是93岁和95岁。他给后世留下了共计360分钟的口述。他4年前辞世,享年102岁。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

凤凰娱乐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