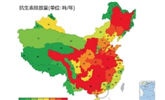陈佩斯任喜剧论坛主席:不能再让中国的戏剧历史中断
2014年12月23日 09:51
来源:凤凰网娱乐
凤凰网娱乐讯 2014年12月22日,北京喜剧艺术节首届喜剧论坛在京举办。作为论坛主席,陈佩斯指出当下喜剧艺术缺乏强有力的评论监督这一现状,并为国内首个喜剧评论团的十位成员颁发聘书。 本届喜剧论坛以嘉
史航:现在好玩儿的电影很饥饿,也很惆怅。也许每个人一辈子看喜剧或者称为喜剧的,有喜剧标签的作品都有个定额,但有人幸运,可能看的十部有八部认为是喜剧。咱们之所以在这儿讨论,就是希望让每个人喜剧定额里头,最后心甘情愿不想退票的人多一些。
姜昆:为什么希望一个氛围形成,大家共同来支持喜剧,来支持那些为喜剧事业奋斗的人。为喜剧进行创作的,因为现在社会条件不足,只能采取互助的方式,我也特别支持。我自己也在投资非常多,我有自己的实验,叫《姜昆说相声》,采取大屏幕和我结合的方式,我说说相声一路走过来的经历。但都是属于个人奋斗的状态,国家不可能在这方面给你支持。我觉得这个队伍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形成这样的氛围大家共同来支持喜剧。
史航:我们关心喜剧的从业者他们一直在忙什么,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很多时候喜剧在不同道路上会师的事情,特别关注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包括姜老师说的卓别林的片,以往喜剧由于体制、艺术形态说教比较重,我们喜剧赢回观众比较难,以往有那么漫长的说教期,结很多善缘这是非常辛苦的过程。
束焕: 参加这个论坛我个人有点乱入感,我最近其实在做影视,我们跟剧场也有点关系,我们搞了六年春晚,春晚小品是世界上最“变态”的东西。既然从《泰囧》起头,回答姜昆老师的问题,因为《泰囧》本身是公路片,那个故事大概分成九部或者十部,每部是根据人物的旅程不断地更换地点,每更换一个地点就是一部戏,我们把每一幕打造出来。这其实跟喜剧特别像,每一幕里头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人物命运,这个人物在这个点上他所遭受的处境是什么;第二个是人物关系,两个主要人物在这里面他们俩在干嘛,他们俩关系到了哪儿;第三个喜剧情景,怎么把这一幕变成好玩的东西。我们特别机械的按照这个方式,我们特别遵循所谓的人物关系一定有一个起伏,最后一定是最高潮,最高潮前面是大低谷,大低谷前面是次高潮,我们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东西。整个拍摄下来之后,总结出了一个创作规律,创作一定是有规律的。
我虽然自己跟戏剧舞台创作离的有点远,但是我们一直在搞喜剧,主要是影视。我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我也接触了很多创作团队,我觉得现在的喜剧创作应该是集团化的创作,应该是一帮人在一块聊。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有两种不同的创作走向,一部分是从科班出来的,现在我创作的时候我来负责做结构。我在2003年的时候跟学生分析过《流星花园》的人物关系,《古罗马》的人物关系跟《流星花园》的人物关系是一模一样的,说明这隔了两千年其实喜剧规律的东西是不变的。剩下的年轻他们大量的把新鲜的东西往里装,他们可能在流水线上负责生产,每一句话、每一个包袱,他们的思路有时候我觉得没过程,现在的喜剧乱翻,是不讲理的。
我在春晚的时候会到开心麻花,哈文跟我说你是新有结构往里放包袱,麻花是六百多个包袱,从里面找一个主题。后来我也去剧场看过,现在的好多喜剧创作,演员其实是被观众“绑架”,现在现卦的东西观众特别认,观众一波又一波的鼓掌,导致你不需要人物结构,你就讨好他们就可以了。有一年正好央视大火了之后,我去看《赤壁》的舞台喜剧,它里面有很多社会形态的东西在里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喜剧创作,我见过很多团队,包括央视的栏目叫《喜乐街》,是一个非常即兴的节目,但是也是来自于非常严谨的人物设计,怎么让演员去即兴,怎么让情景不断地发生反转,现在喜剧创作有几条路,不敢说是殊途同归,但是能反映各种各样的现象。有的时候现场的效果不必在乎人物的动机,但你想要做一个真正经得起检验的东西的时候,我自己发现每一次创作都是第一次创作,比如说我东西弄完了之后,上台之后,我发现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全部是最基本的问题,一个可能是这个人是谁,他打哪儿来,他要干嘛,你会发现你没分析清楚。可是你又想这是不应该犯的错误,创作你永远在犯同样的错误,到最后你会发现答案不重要。
戏剧的推动力,人物为什么会这么做,你回头想原来是你推动力本身出现的问题,导致推动力不够强的时候,你的人物开始都是从不得不开始的,喜剧就是一个人被迫做他不擅长的东西,喜剧一开始都是不得不把你放在困境里,人物解决主题的时候是需要选择的,尤其是在爱情戏里,为一个女人他做了,自己在剧开始的时候打死不会做的事情,但是我老觉得这就是规律。当你把一个故事写完了,你发现不对的时候,别人指出来的时候,我怎么没出现这个问题呢,后来会发现自己在犯同样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创作,恰恰这就是说明是最重要的。
首先喜剧是有规律、有方法的。我一个朋友说喜剧不需要你有幽默感,你有技巧和方法就行了,我觉得还是有点幽默感才行。我觉得现在的喜剧创作,是不是也得需要正本清源。是不是在每一个新的喜剧人才冒出来的时候,因为你经过市场的锻造,你面对的是这些观众的时候,你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笑料是最重要的,你最后积淀下来的东西,你发现喜剧继续往前走,你还是回到最简单的命题,又回到在大学里书本上学到的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们做喜剧的时候,反而会对曾经藐视的东西重视起来。包括我接触到的,在我自己喜剧创作团队里,有很多不是科班出身的,比如说搞计算机、金融的、搞种子的,但是他们都很优秀。他们一开始是抱着藐视这些规则,最后经过一次创作,写完之后他突然发现原来真是这样,他回头又重新拾起这些书本。
我这几年一直不停地在做喜剧一线创作,现在试图想组建自己的团队。我觉得喜剧论坛,我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最后做一个正本清源的工作,告诉大家喜剧还是一个传承和回归。
史航:他说了很多创作规律,我们找创作规律不一定要规律化的创作,要有幽默感,要有很多灵感。现在请一位远道而来的,我一直认为是灵感达人的詹瑞文老师,谈谈你心目中的喜剧。
詹瑞文:早上已经说了我的一些感受。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很重要,我们在很早以前对喜剧这个工作有灵感,有感觉的人,其实都在累计一些我们的经验。但是我们从后现代主义,我们不断地打破之前我们建立的东西,但是又回到之前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肯定的过程。我作为一个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同时间每一次创作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种新的可能性在里面,其实我们找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这个时代也在往前走,我们都是不断地发现新的东西。
我最近跟徐峥聊天,他还是一个不断地要发展,跟我们爱喜剧的人一样。他在香港去拍他的电影,他找我帮他和演员做培训,他作为演员的时候他也有新的发现。我们做了几轮以后,他又回到说其实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很基本、很简单的东西。当但我们在一个行业里面的时候,我们都忘了最简单的东西。永远好玩的东西就是激发我们的一种笑点,有一个点出来陈老师做、我做、金老师做都不一样,因为我们三个是不同的,但是他很中性。所以我觉得剧本创作上结构很重要,在结构里面演员还有导演在进入这个过程里面,必须要顽皮把它走出来。但是走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规律,我们在这个光线里面去玩,我们不会走到别的地方。在之前我们的概念限制一个游戏的规则,但是在里面,在拍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很顽皮的状态,我们看见一种瞬间的我们觉得很热的感觉,我觉得观众都爱看这个东西。如果观众欣赏一个喜剧作品,是因为他们知道笑点在哪里,规律在哪里的时候,其实不好玩。我看戏我就看演员,我看演员的时候必须让我们忘了这个是什么戏,我要看我就跟着他,因为他代表我,同时间我作为一个观众,其实我是透过他来看自己的故事,这个永远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我们的脑子只是想一个故事,但是观众用我们的故事去呈现自己要看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规律,我们的规律帮助观众进入他自己的世界。里面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是他们疯狂,他能这样做太好了,在我的生活里面我不能这样做。
我们的工作,我非常非常开心,在不同的行业里面,我们有一些人都非常非常专注来做一个剧本的工作。好莱坞他们都有一些很专业的人,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好的剧本出来以后,其实最重要的是里面的人怎么去玩。前段日子看到一个街舞3D,里面的故事很好,跳舞跳得很好,我看拍的也很好,但是缺的是什么?就是一种在里面角色好玩的灵魂,他们很认真的去做这个东西。我们都是很认真的人,但是他们要很认真的玩,才可以出现一种有共鸣、有吸引力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在不同的范围里面我们都来交流,其实谈完以后可能我们私底下会变成朋友,我们在咖啡桌上再谈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得出一个结论,而我们得到一种频率,我们的频率是做一些好玩的创作。无论在电影、电视或者是舞台上我们才会另外一种状态。演员是很奇妙的,你叫别人去做他的东西,哪怕是同样的一个桥段出来也觉得不行的,做喜剧演员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团,有一个很强的架构,让演员在这个游乐场上都玩的很开心。
史航:当时詹瑞文老师说到玩,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玩是很重要的,这样让我们人格和人生都很完整。其实很多时候排喜剧,就是聪明人下笨工夫,要不是聪明人做喜剧其实很难,但聪明人下聪明工夫,可能很多时候他是使巧劲,各种资源共享,各种信息荟萃都可能是个办法,但是聪明人下聪明工夫,你不会老是聪明人,所以聪明人下笨工夫你永远很期待。
陈佩斯:尽管社会上对《泰囧》评判完全不一样,各自都有各自的评判,但是我觉得束焕进步了,因为你在实践当中发现了方法,你没有走弯路,你有所得,而且这个所得不是像别人说的是获得了多少票房,而是你发现很多有规律性的东西,你在学识上上进了。规律有多重要呢?可能它会影响到人的一生。我们当初做小品的时候,就碰到这么一个良师益友,就是碰到姜昆先生。我们第一次去中央台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个我们自己做的小品,那时候戏剧人排练的时候那种形式做了小故事,我们希望有点幽默感,但是别人可能不乐,我们自己觉得特别开心,人家看着傻傻的,不乐。后来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做成以后,我们到市场演出,到了市场你演的好就高兴,你演的不好就不乐。你是个名人,期待特别高,越看越冷,越看场子越觉得凉,这个时候觉得特悲哀。你自己对喜剧的东西和你实际的表述能力差的太多,在完全不知情情况下演喜剧是很悲剧的。我们1983年的时候把我们的套路忽悠一遍,姜昆老师就告诉我们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把错误接受下来,你反应的要慢于观众的认知就对了。包括结尾怎么结,结尾的韵律感必须要快。我们在使用的时候经常的违背它,为什么呢?那时候个性很强,那时候人都有个性。到了场上立刻给你颜色,你期待还要更好的时候,笑声没了,迅速的检验我是错了,这样就把规律性的东西固化了,我们的演出就势如破竹,然后就被社会肯定了。
和我们同时代,也是做电影的,也都上这条路,这在到处巡演,但是走到哪儿包袱老是冷冷的,不温不火的,最后演着演着从舞台市场就消失了,最后只能在电影上偶尔幽默一下,一下注定一个人一辈子朝着不同的方向去走。受益的方法之后,我们做了很多,我们总结方法,一个组合一个组合曲做,最后我们才知道一千几百年以前我们祖上就有了这种类似的喜剧形式,原来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自古就有的喜剧套路,这种讽刺都是自古就有的套路,而且人家用的比我们还跳,还大胆,所以像这种计谋喜剧都是很古老的喜剧手法,大家总是在重复,规律性的东西不可逃避的永远在重复,但是故事换新的了。我们怎么能发现最根本的规律,然后再用它变换万千。非常值得祝贺的束焕发现的是有规律的,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发现的,有很多人认死理,他就认为自己是对的时候这就错了。
《泰囧》的成功有它的必然性,这是一个社会的需求,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一个正常、平和、宽容、健康的社会需要这种节目,而且这种节目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符合市场需求的、大众喜爱的作品如果就偶尔出现,这个社会还不够健康,我们还要再健康一点。不管怎样,它能偶尔的出现也是社会的一个新的契机。想当年吃面条也是偶尔的现象,然后就引起了一个轰动性的效应,当时也有多少人批评这些不健康的东西,不严肃的东西,批评声远远大于欢呼声,因为他们是主流的声音。
我们后面的工作,最好是能够经常性的,把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总结出来,把这些经验告诉给你身后学弟学妹,这些东西要给他们,给到他们之后他们就能少走很多很多弯路,这个社会进步的速度才能快,量比较得够才能出精品,不能期待我们现在制作精品,精品能像大工业生产似的就出来,我根本不相信,汽车可以、坦克可以、飞机、大炮可以,唯独艺术不可以。我们不能用工业的常识来指导艺术,所以我们力图要打造精品的时候,一定打造的不是精品,精品只有通过市场自然的淘汰,经过一段反省,甚至社会也可能是精品,大家都不认识,可能过一百年才发现那个东西真好,我怎么当时就没看,最后说完了,看不着了,过去了。《泰囧》当年没看,你没看《泰囧》就忽略了那个时代,这种有标志性的东西你没去看你就忽略了一个时代特征,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征,而这个艺术品就是特征性的物体。
姜昆:年轻人现在不按规律出牌,我把80后叫到一起,我脑袋在琢磨,我们当时也编包袱,大家说绕口令,绕口令里找包袱,年轻人说绕口令就越来越上路了。
史航:死理和规律是两回事,死理是一招吃遍鲜,十五年之后还是来这一套。而规律就在于是个标准,随时在捕捉有趣的东西,不是搜集一个死理,而是编织很多活的道理。大家研究规律,在一起聊这个,不是最后变成宇航员吃牙膏式的食品,但身体很需要,你的胃口受不了。喜剧又是机械又是反机械的,规律本身也是规律的敌人。刚才我们说到电影《泰囧》有很多受众,它代表偶尔和必然。
今天的第一个题目喜剧的现状,有的过剩或者不够都有忧伤的地方。
徐昂:刚才姜昆老师说的都是对我们知识上的补充。今天上午谈关于喜剧论坛,刚才我听了几个不同的标准,标准里面有一部分说以发笑为标准,还有一种类型对生活的扭曲,可能也是某种喜剧。
刚才提到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问题,我是有一个感觉,我从悲剧开始聊起,前一段时间《雷雨》,我们认为是叫做经典的悲剧。这个悲剧在首都剧场经过演出之后,严格意义上变成了一处通过悲剧串联的喜剧。当时演出的演员受不了,就像一个喜剧演员上台演一部喜剧之一,他做好了心理准备。一个悲剧演员在笑声中死去是很难过的事,后来演员们提出了抗议,就说我们以后不要把票卖给学生观众了,我在餐厅里面不允许某一部分食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们在排戏的时候,是不是变成了清真餐厅。
陈佩斯:他把不笑当作一个宗教仪式了。
徐昂:是不是会把笑当作某一种宗教仪式,提到仪式这个问题,那天我看了一本书,我是属于教条主义那一派,书里写了人为什么会笑,举了一些例子,从动物开始,人会笑,动物会不会笑,人笑会有某种情感,他发现动物也有笑,孙猴也会笑,它做出这个反应之后,他研究它做出这个反应的核心目的,一种社会化的动物在一个社会群体里面想要上起嘴角,证明它没有食物,所以咱们说微笑服务也就不难理解了。令观众发笑,观众在心里面某种程度了败给了这个戏,你的行为是有某种预谋的,让我做出的相同的理解,在某种情况下我被你操纵。在这些问题上,刚才我说的悲剧上发笑是我们的常识与通识变了,有的时候我看一个喜剧,我如果没看懂的话我不会真的发笑,哪怕是一个包袱,现在的观众和以前的观众常识和通识了变化,当我们提到一个概念的时候大家可能产生不同的感觉。
姜昆:当时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看法?是因为本身结构导致的,还是因为时代赋予的内容引领?
徐昂:大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知,认为观众没受过教育,受教育程度低,所以看不懂这样的戏。说我们要去规范人的意识,这是很荒谬的。另外一种划时代的,以他出现的时代在这之前没有这种类型,而他出现了之后产生了某种类型。还有一种叫做里程碑,这种戏很可能是某种划时代,但是不能称为经典。
陈佩斯:2006年我在上戏,孙老师请我讲课的时候,十多年我一直在研究人类笑的行为,我给喜剧和笑下了一些定义,笑了很多条件产生。我们就这个事件,不管是要叔叔杀掉父亲,儿子要替父亲报仇,这个关系和过程都是喜剧的过程。《雷雨》的人物关系其实已经成为了喜剧关系,只是被当时的社会欢迎包着,包成了一种悲剧的范围,因为他违反了伦理,这是天地不容的,大家一直抱着天地不容的心情,已经被宗教仪式化了,生活当中被仪式化以后,后来变成经典剧欣赏,我们必须要怎样,不能怎样的时候,偏偏我们碰到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把这一切都去除掉了。我们可以不按照这些包裹的思想去正常的欣赏一个艺术作品了,结果本体的东西就暴露了,本体的东西就是喜剧。他犯了一个喜剧重大的讨论,要失去交配权喜剧,而且有一个伦理错位喜剧,都是在大喜剧粱子上,要不是喜剧都见鬼了。过去的人不笑,是因为过去的社会不正常,不健康。
姜昆:你说孩子们笑过去的伦理仪式。
史航:我特别关注这个新闻,我去看了后续报道,当时的在场观众反映在哪几处笑。周冲少爷对武大海说那么你不生我气了吧,我们拉拉手好吧。周冲当时在那儿说的,曹禺写的时候觉得是劳工神圣。时代在漂移成两个国家了,但是划时代又会被时代划掉,这一刻你用它划时代,下一刻它把你扔掉,下一个时代就会到来。在喜剧大粱子上做文章,有人关注,自己也是有心得的东西。笑是一个呼救的信号,在人间需要一个补偿的东西。喜剧就是带人生活到别处去,喜剧永远是一个逃避,但逃避有时候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逃避是消极的,所以喜剧有时候帮人求生的东西。
史航:我们特别关心在第一线的创作团队,创作者又得研究、分析、改进又得寻觅。请田水女士发言。
田水:我这次来要向各位老师学习的,我自己是演员,我用我自己演戏的心灵来说,我是很怕演喜剧的,我觉得喜剧从表演上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于我自己来说,在台上去演一个人物,让别人流眼泪,可能更容易一些。我觉得喜剧表演分寸感会非常重要。刚才徐昂说《雷雨》,《雷雨》在话剧中心演出的,我们的出票情况,《雷雨》是第一个四五场演出票全部卖光,而且是一票难求,包括我们自己演员进这个剧场里面看戏,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首场演出我看了,是媒体场,并不是公益的学生场,但是还是有人笑了。我是觉得《雷雨》对于我们上海的观众来说,大家发笑的原因是舞台的表演状态,尤其是上海很多观众,已经不习惯老的北京艺术家在舞台上的表演状态,他是觉得很隔膜,小剧场跟大家很贴近、很生活化的一种。南北表演上的差异,比如说上海的滑稽戏送到北京演出,我估计效果也不是很好,北方人认为上海劣根性的东西通过语言表现出来,他觉得这种东西他不接受。《雷雨》各个艺术家在台上演出,很多表现状态是观众们不太接受的,周冲一上来就笑了,他的装扮,他说话的感觉,他拿一个羽毛球,脸红扑扑的,他说在北京人艺演了十年的周冲,就是按照周冲的形象招进去的。确实好多年轻人对于这种人物关系他有自己的看法,他是觉得你周平是公子,怎么就不能带着心爱的女子走,这种男人没有出息,很多人有这种看法。
我们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做的很多喜剧, 我觉得从原创根源来讲跟北方不是很一样,第一受上海地域的影响,大家真的喜欢看外国戏。喜欢看外国的原作的东西,我们演了大量欧美比较经典的,通过市场检验的戏,而且在上海演一轮两轮也是通过观众检验的,还有何念导的具有喜剧因素的话剧,大家看了也挺开心的,它既有喜剧因素,它又有外部的手段,通过一首歌把它表达出来,这是我们上海观众真的比较喜欢的。无论是从表演状态上来说,还是从创作上来说,地区的差异还是存在的。
刚才数据上很多观众喜欢这个戏,很可能他就喜欢这个演员,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喜剧的创作他不问出处了,他生拽,他就是看我喜不喜欢在台上的演员,演的好不好,大部分观众已经不会像艺术家去想是不是在情理之中,他就是意料之外的开心,所以我觉得演员的状态还是很重要的。陈佩斯老师在喜剧教育过程中,把你对喜剧表演,如何把剧本当中的东西通过您的经验传达出来,您这方面经验是太宝贵了,告诉年轻人该怎么样正确的演一个喜剧,正确的体验喜剧的精神,把它表达出来,可能对我们观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陈佩斯:对于观众不重要,对于要走向喜剧的人是有关系。
史航:你刚才说到观众现在是不一样的心态,有的人只想看意料之外,同样一个剧场有人当博物馆,有人要当植物园,有人当动物园,有的人直接当游乐场,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每一种剧场都有,每一个剧场不同的时令有不同的东西。
武晓南:我们和陈佩斯合作两年了,我是纯以票友的身份在专家面向献丑,我就是看戏的。我感觉喜剧这块,我自己的理解可能不成熟,我理解逻辑错位的东西就可以出笑料了,只要是逻辑错乱了,就有喜剧的成分。你看到非常的东西的时候,如果你足够强大,看妖的时候你可能是藐视的笑,有人提到说笑可能是恐惧的笑,我们看到妖的时候,你觉得你没有见过你就恐惧。逻辑的混乱其实很容易,要说简单也很简单,但这就像路边捡的,快得很。但是陈佩斯老师这样,多少年从结构开始动。我第一次见陈佩斯说,你演的《谁是主角》,枪的带子断的,每次电视台重播,我一看收视率绝对高,挺好玩的。最后我发现说您枪带原来是断的,最后陈佩斯老师把枪挎在胳肢窝底下了,后来陈佩斯十年打造这几部戏,我看了《阳台》,特别有喜剧的结构在里面。每一个包袱不是硬塞进去了,不是说为了逻辑的错乱而错乱,把它给打乱了。而且顺理成章的到这一步了,自然就有一个非常的东西展现在大家面前。你要想打乱逻辑凑一点很容易,但是真正能够慢下来创作喜剧,把什么慢下来呢?咱们讨论创出经典急迫的心情慢下来。我们就是去体味生活中哪些在生活中出现了,但是没有被人发现,发现这里面有一个错乱的逻辑,不是说发现了一个把它简单堆积,而是说顺理成章的把它研究下来,这就是大家刚才说的规律。刚才我也特别感兴趣徐昂老师说的看《雷雨》的时候怎么就乐了,大家一听,你们还专门为周冲招一个人,一说大家就乐了。
王翔:悲剧是把美好的事情给人看,喜剧是让人把奇怪的事情那它当笑料谈出来,意义同样的重大。欢迎各位老师去看《顾不上》,24号开始。
我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向陈佩斯老师致敬,这是最主要的目的。我们讨论喜剧很好,但是也许我们还有机会讨论什么是真实的喜剧,不管是文学的喜剧,还是艺术的喜剧,还是商业的喜剧,真正遵循规律的喜剧是什么?我们有一点尴尬,本质上真实的事件,但是可以借助讨论喜剧的方式来说,但是我相信总会有机会敞开谈。
史航:现在请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对这个喜剧发言,首先请孙惠柱院长。
孙惠柱:大家都在说规律,规律这两个字在学校里一直有争论,第一线的人经常不屑于规律,总是打破规律,但是又不能不说。有的规律更容易打破,有的规律不太容易打破。我从不太容易打破的规律说起,老百姓喜欢喜剧,这个规律打不破。还有一点政府是一般不喜欢喜剧的,这个也很难打破。刚才姜昆老师说到,文革前,这个跟陈佩斯说的不一样,那个时候的时代肯定不如现在好,倒有不少喜剧电影,从比例来说那个时候还不一定,但是这也不说明问题。舞台上1949年就没有出现过喜剧,一出就批判,大家就不敢弄了。改革开放以后八十年代的时候,出过非常好戏剧喜剧,现在没有了。政府关心的多了,钱投的多了,精品工程、五个一工程一来喜剧没有了。现在是京剧独大,几乎想不到喜剧为主角的,那些都不是京剧,现在是越来越集中到政府掌控,然后剧种当中,京剧是京剧,其他全都是地方戏。陈佩斯要是演戏剧喜剧,那不可能是京剧,其实你什么都可以学的,但是一定是地方戏,现在以后没有了,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我是到这儿发政府的牢骚,我倒是更想抱怨是我们这圈人的,我自己跟我们的同事、学者们、教授们起了很大的坏作用。为什么?首先戏剧理论几乎全是西方的,所以陈佩斯拿《张协状元》做例子我非常赞同,其实这个我早就知道。差不多九年前,我们知道中国戏剧传统当中,不管是喜剧还是其他的剧种,我们都有很多好东西,但是绝大多数的戏剧学者不看。西方的理论才最牛,最近这阵儿北京最热闹,连番轰炸都是西方大师,戏曲跟戏剧界的人没有关系,戏剧、戏曲学这个词就是最大的问题的根源。好像戏曲跟我们没有关系,其实全国研究戏剧历史和理论的人,算总数戏曲学者多得多,但是这个跟戏剧界好像没有关系的,他们基本上只研究文本。你看《张协状元》,看到他的表演方式,但是有那么多的学者,那是成百上千的,好像跟我们第一线的人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学术布局的失策。这个倒不是政府要你这么做的。他们选简单的事,再加上,戏剧界也不会去找他们的,因为你只知道研究唱词。
反过来研究外国戏剧的,外国戏剧只讲理论,而且近年来,其实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没有工夫去看剧本,我们政府多花了那么多钱,结果交流的效果反而更差。我一个月之前到中国戏曲学院去做讲座,因为我经常去让我搞一个新一点的题目,找一个新一点的题目,我的题目叫做《习大大书呆与国际交流》,我第一个问题是故作惊人之语。我说什么时候你们说什么年代,国际交流的效果最好,应该说现在我们看到那么多外国大师的戏,其实效果最好,文革的时候谁都没有。为什么习总书记那个时候读了那么多外国的书,其实图书馆里封着的,被人开了封拿出来了,这些书他记住了,他记住了《悲惨世界》、记住了《老人与海》,应该说这些包含人文主义思想的西方经典,说的夸张一点将会影响世界的未来,因为影响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主要是在那个会上他抱了那么多他喜欢的书,内容其实最重要,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手法时候。那个时候连电影都看不到,没有看到任何戏剧,这些故事我们记住了。
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们自己请人进来,包括我们派人出去,学校里有很多出去,就跟旅游者一样,就是看一些文盲也看得懂的东西。以前我们怪外国人不理解我们的戏剧,外国人说我们戏剧演员就会翻跟头,没有内涵的。我们老是给他们看《三岔口》、《闹天宫》,认为他们是看不懂我们的文戏。那么现在我们反过来看外国也常常是这样,我们选外国的戏,我们自己出去看也是看一些不用听的,要听的话花多少力气。像陈佩斯这样花很多力气看古代的剧本,这个时候花力气了。现在大家都浮躁,不单是一般老百姓浮躁,来学者都这样,还使得大家以为全世界的戏剧都已经是不要剧本了。所以越来越不注重,所以我特别欣赏陈佩斯做这样的努力,八十年代,仅仅凭他的表演,根本不需要去读剧本,不需要去研究这些东西,他完全可以大火,结果他还闭关几年。他写《阳台》之前他读那么多剧本,工夫用在剧本上了。这个剧本我当时将近十年前我看到的,那时候我根本不认识他,那是大明星,我看了以后,我在我的学生当中说,一般的学生没有办法,进修班都是专业剧团的人,你们谁有办法帮我找到陈佩斯,有人就说陈佩斯的剧本都是枪手写的,我说这个《阳台》如果是枪手写,我倒要认识一下这个枪手。中国好的编剧我也认识一些,有谁愿意隐姓埋名,拿多少钱写这么一个剧本,不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
昨天晚上再看一遍,更加证实了我的看法,刚才我们在讨论经典,我非常徐昂的看法,有人让我编一本百年戏剧经典,我就没有把《雷雨》放进去,曹禺有很好的剧本不是他的第一个剧本。如果说《雷雨》是经典,是处女作的经典,任何人一辈子写第一个剧本写得那么好,那是不得了的。把他所学的东西全部放进去了,所以当年就有人做。我最近发现了李健吾那些懂外国戏剧的人一看这个技巧非常好,但是学别人的,学别人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中国没有的时候,需要这样的剧本。到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他里面融进了三个四个五个外国戏剧的故事在里面。编剧形式完全西方的,语言完全中国的,非常了不起。我当时就拿《阳台》这个做比较,我说这个戏也是用一个完全西方的形式。我刚才听王翔老师说闹剧不好,实际也反应了社会上对喜剧还是有偏见的。闹剧好像中文语境当中就属于不好的东西,就是让人笑的。
我在见到陈佩斯之前,成为朋友之前跟他在报纸上打笔仗,一位记者帮我带话,我跟很多人说,你们谁能够帮我带话,带到陈佩斯那儿我谢谢你,带什么话?一个是我非常欣赏他的《阳台》,我希望请他到山西来教课,陈佩斯还没有见到我,已经在报纸上搏我的说法,我的说法就是刚才说的,我认为像《雷雨》一样把一个经典的西方的编剧形式、叙事方式,那种三一律的方式,其实《雷雨》还没有完全做的三一律,这个是完全做到的了。和完全中国的故事结合的天衣无缝,相比之下这个还要好,因为我刚才说了曹禺故事,都有三四五个故事看得出出处的,希腊、法国、挪威、美国的都有。陈佩斯的故事没有一丝一毫是外国的,外国不可能有农民工的故事。跳楼秀的故事,因为那个时候跳楼秀刚刚出来没多久,现在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十几年前是刚刚出来就已经进去了,在这之前我就呼吁,我说中国那么大的社会现象,农民工现在从来不在舞台上看到。
前两天跟田水还在讨论,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农民工怎么可能买票看戏呢,你就是想写,能写好,那也不能演,没有人看的。他不但把农民工作为主角,他自己演。而且能够做得那么火,就说明了农民工也是可以入戏的,而且可以如此的吸引人,以至于人家都忘了这个戏,贴标签是农民工的戏,当然你也可以他是反腐的戏,那个时候其实都没有想,现在来看两个都是重大的问题,中国社会的大问题,农民工的问题,拖欠公司是太普遍的问题,还有反腐的问题,中国最大的两个问题都进去了。因为你毕竟不是曹禺23岁的时候,23岁时候写书,《雷雨》很了不起了,所以你不能要求它多么成熟。曹禺家庭使得对中国贫苦人不了解,鲁大海肯定是不真实的,周冲其实像他自己现在看来都显得不真实的。但是陈佩斯因为他的社会阅历,他对西方形式的研究跟曹禺很不一样,曹禺不知道读了几千个外国剧本,把他化为他的剧本《雷雨》,佩斯只读了一个就够了,聪明人只要读一个。那个时候他没有跟我见面的,他说我是个农民,我是不会受西方影响的。后来我见到,我说你是农民,你农龄几年,他说三年,我说那你比我差远了,我在江西山沟里待了七年,所以是不是受系影响,跟你有没有当过农民是没有关系的。
绝大多数中国人通过翻译来受西方影响,不是直接读原版,他只读了一个剧本巧了,《借我一个男高音》,这个承认一点都不丢脸,曹禺那个时候不太想承认,这个规律。他后来告诉我那里面有六扇门可以躲人,你写到五扇加不进去了,再加一扇怎么也加不进去,说明学这个跟三番四斗是一样的道理。后来他说我用窗帘,落地长窗的窗帘,等于也有六个,我说我认为你比他还高明,你有七个,高明是高明在量化上面,因为你自己钻到床垫底下,你有七个藏身之处,他只有六个藏身之处,加一个是非常难,一个两个很容易。加到五六七个是非常难。佩斯学了西方的,但是他把整个技巧提升了,思想也提升了,我也看了不少这样的戏剧,但是这些都是纯娱乐性的。《阳台》到最后真还跳了楼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所以他有思想性,可以说他俗俗到底了,台让那么大一张床,好几次说了,这么大一张床,多少观众指望着看床戏,就是没有看成。但是最后他思想境界提升了,从这些角度来看,佩斯学西方是为了超过他,他第一次就超过了。《雷雨》学西方,不能说超过他,只是画的非常好,但是在中国成熟的剧本还是沙漠的情况下,他能够写出这么一个戏也是非常重要。佩斯的时间不一样,不是拿跟曹禺比功劳,在这个时候也可以说是必然的,这两个剧本的比较非常重要。他老说西方不要他,其实你自己也得益于西方,但是你的不同是你学了西方的东西要超过西方。现在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我们跟学生说西方不学不可能。但是现在整个依据理论界掌握话语权的人只讲西方,甚至包括在你的中国戏曲学院也只讲西方的理论。所有的剧本表演理论全是西方体系。学了以后要用信心,我们要拿来为我说用。
讲到喜剧表演,去年秋天,剧协在那儿搞中日韩时戏剧节,厦门弄了一个半天的喜剧工作坊,有法国风格的,由美国风格的,也有高甲戏,我觉得最好的是高甲戏,也可以说法国风格都是学生来,不是最好的大师来。我就说我希望你们高甲戏什么时候到上海戏曲学院去,一个为首的演员四五十岁了,很高兴的说我去了,待了一年,他去当学生去了,我说当学生也好,但是你不要只认为我们这个戏剧界的气氛就让戏曲员听到要到戏曲演员就是当学生,去学斯坦尼,我可以去教我们,他有十几种表演丑角的风格,我说全世界没有,因为生旦净丑,一个戏里面最多两个丑角,再加上一个踩脖子,就不会多的,那个剧种全是丑角。像《阳台》这样的戏要用戏曲板,那个个都是丑角,全世界找不到。欧洲现在硕果仅存的假面喜剧,他有好几个种类,但是现在也找不到八种。这么好的东西,从《张协状元》里面学我们的喜剧传统是一样的。首先我们中国话剧演员也可以学,上戏我们花了很多钱。外国人进来教你玩一些游戏算了,我们的戏曲还有系统。
国际剧协到文化部说过了,国际剧协要搬到上海来,那个会长是瑞士人,他来中国很多次,也看到中国很多好东西,我们一起来联手做,就拿中国的喜剧表演,写剧本太复杂,喜剧表演语言障碍也不多的,他八种喜剧表演,我们各种各样的,包括詹瑞文这样的,也许国际剧协到了中国,除了他做常规的工作,他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借这个平台来向全世界推广我们的好东西。我们的好东西里面就跟佩斯想的是一样,喜剧相对来说更容易打破语言障碍,悲剧是更难了,可能明年后年我们就要这样做。
我归纳一下,一个陈佩斯上午讲的题目,我们自己有很多好东西不要丢了,西方我们也不否认,《阳台》编剧结构里面给我们受益很多,他们的好东西并不仅仅是后现代,后后现代那些表面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引进的理论中国已经太多了,真正人家的好剧本我们不知道,我们都只看表面的花哨。最后喜剧角度来说,美国和英国当代剧作家当中,最成功的两位剧作家,自己的剧作赚了很多钱,绝大多数中国戏剧人都不知道。英国那个人到现在中国人还不知道,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请一个他的朋友,英国皇家戏剧学院的前副院长排过一次,但是专业剧团从来没有演过,这个剧本既有传统的东西,但是打破了第四堵墙。这个人二三十年来,每年自己写一个剧本,自己制作,自己导出来。北京要么是廊坊、或者承德的地方,不是在伦敦,他去一个学院演一下,第二年到伦敦西区去了,其实它有它的特点。三层楼的房子,但是他规定不可以搭楼,必须把三层的家具全部放在一个平面上,通过你的表演让观众不会弄错的,看清楚,你现在是在一楼、二楼还是三楼,很有创新。但是我们介绍了那么多的东西,这样的剧本北京从来没演过,上海话剧艺术院也没有演过,演不了。
我们把阿尔托这些,不是主流,他们也不想入主流,也永远成不了主流先锋的戏剧捅的那么高,北京、上海还好,其他城市根本都没有,到天津、武汉、沈阳要去看戏没有的,沈阳二人转是有的,要看话剧是没有的,这在全世界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钱花了不少。刚才大数据,我们要知道每天发生什么事情,我希望要加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到每一个城市,问人家说你有没有看过喜剧,我六十多岁看过戏,这个意义不大。两年里面你看过几部戏,每天晚上,一个大城市外地来的人,如果晚上要到一个演艺场所去看演出,有没有,北京、上海是有的,如果有的话有多少。前不久到亚美尼亚,那个城市我去之前也不知道叫什么,埃里温首都参加国际剧协的大会,那个地方全国只有三百万人,那个城市几十万人口,我们晚上到了以后,出去吃饭的时候,随便一走,走到一个大歌剧院,这么小的城市,二十分钟之内八个剧场,每天晚上有七八个时演出,这样的指标我们要了解,至少要慢慢知道北京、上海平均每天晚上有多少演出。正式卖票纽约是一百多个,伦敦应该也有一百个,其实东京最多,但是都是小剧场,东京有三百,首尔都有两三百了,都是小剧场。这些数字比60%看过戏都重要,看过戏我说二十年前看的也算看,对现在意义不是很大,这个做法我觉得很好。我们的学者常常只看到了冰山上一点点,说这个大师厉害,这个大师跟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在他自己国家也没有国家,到我们这儿来也没有关系。我们要知道普通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的舞台上的文化艺术。
[责任编辑:张园园]
网罗天下

凤凰娱乐官方微信
图片新闻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